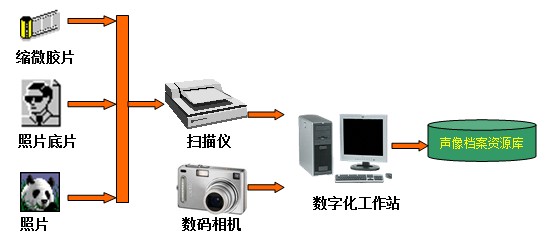Peter B.Hirtle
(Peter B.Hirtle是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教育、研究和信息服務部主任,曾擔任康奈爾大學數字文件匯集部的主任。同時,Hirtle先生還是D-Lib雜志的副主編。他是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2003-2004年第58任年度主席。)
編者的話:
在2003年8月21日于加利福尼亞洛杉磯召開的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年會的開幕式全體會議上,PeterB.Hiltle主席發表了這篇講話。
今年4月,華盛頓郵報報道,Bob Woodward和CarlBemstein的文章被以5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給了德克薩斯大學的Harry Ransom人文研究中心。“水門事件”丑聞的大部分都是這兩個人披露的。華盛頓郵報中的文章稱還有其他一些文章以大約相同的價格出售,其中,SusanSontag的文章賣了110萬美元,Francis Crick的文章賣了130萬美元,Zapruder拍攝的肯尼迪遇刺的膠片賣了1600萬美元,溫斯頓?丘吉爾的部分文章賣了1840萬美元。其實,報道中可以引用的收購方面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2000年美國政府花了1800萬美元購買里查德?尼克松的文章,或者Sotheby向國會圖書館提出以2000萬美元出售馬丁路德?金的部分文章,經鑒定,這些文章估價為3000萬美元。
對所有的檔案工作者來說,檔案文件可以具有經濟價值并不為奇。我們保管的文件對歷史、文化和價值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如果在e-Bay或拍賣所,這些文件也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我聽說,就在我工作的康奈爾大學,據評估圖書館是大學擁有的唯一最大規模的資產。由于康奈爾大學擁有7000萬原稿文件,比如林肯《格底斯堡演講》手跡、James Joyce的《尤里西斯》的部分手稿,圖書館的大部分價值就在于檔案和手稿文匯集,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簡而言之,檔案和手稿庫房中管理著價值上億美元的資產。然而檔案館一直資金不足。許多檔案館是“捧著金飯碗要飯”:我們有價值百萬的資本資產,卻沒錢雇用員工、維護設備或支付公用事業費用。
由于需要資金,同時又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同時也是值得稱贊的原因)不愿意出售資產,所以許多檔案館就尋求從管理的檔案資料中獲取收入。檔案資料復制品的出售以及為資料用于商業目的頒發許可證正成為檔案館越來越重要的收入來源。
檔案館尋求通過館藏獲取資金的方式實際上是在步博物館之后塵。長期以來博物館一直利用為各種項目頒發許可增加收入。對于某些博物館來說,為其館藏藝術品頒發許可證已經成為資金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可以用來支持教育和管理項目,并把知識產權管理作為一項主要的行政任務。
把檔案館藏數字化也使人們更加注意其可能存在的經濟價值。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數字化的內容可能會帶來資金收益。例如,Lesley Ellen Harris是專門為博物館和圖書館撰寫知識產權問題的律師,他把數字資產看成是“二十一世紀的貨幣”。大多數的檔案工作者都知道商業數字化照片匯集,比如在Corbis,Getty Images和紐約新聞日報上刊登的照片,他們想了解通過利用自己的館藏是否可以和產生類似的經濟收入。很明顯,人們把檔案館藏看成經濟資產的觀點正日益加深。我們也認識到,即使檔案館中最不引人注目的文章片斷,如果我們想將其出售都可以從eBay那里獲得收益。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希望通過數字化可以把固定的資本資產轉化成流動的現金。
我相信,對檔案館藏的商業開發可以采取一種有利于整體檔案工作責任的方式,即將過去的資源變為未來的可用之材。然而,理想中的結果并不是注定能實現的。現實的風險是,對檔案館藏的經濟開發可能會與我們的中心原則和價值觀發生沖突。
所以,在今天上午的會上,我準備和大家討論一下我們擁有的檔案館藏所有權的本質,以及它可能對館藏開發產生的影響。我們經常聽檔案工作者談論保護“我們的東西”,但文獻資料作為檔案的本質是什么?
諸位大都知道我對知識產權問題非常感興趣。我們可以通過知識產權法的一些概念,特別是關于公眾領域方面的觀念了解擁有檔案文件的含義是什么。我想讓大家明白,對公共領域資料的擁有與擁有一輛車或一所房屋的概念是不同的。實際上,對于我們檔案館中的資料,我們并不是擁有全部,有些部分是歸公眾所有的,如果我們想對這些資料采取類似于壟斷的作法,那么就是在危害公共。因而,人們經常在Archives & Archivists listserv上看到的關于使用“我們的東西”的報怨,或是要求對數字圖像的使用采用水印或加密技術的建議都屬于錯誤認識。
為了尊重公眾在檔案資料方面的利益,我們在制定許可證體制的時候要特別謹慎。我認為,如果檔案工作者能在尋求經濟收益的同時堅持我們基本的價值觀,同時尊重公眾在公共領域資料方面的利益,就能夠避免許多博物館因為試圖壟斷和控制館藏而招至的譴責。
知識產權法和所有權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知識產權法關于檔案文件所有權的規定是什么。第一,版權法在某件物品的實際所有權和其版權之間劃分了明顯的界限。一個人掌握一封信、一張照片或膠片并不意味著他擁有其版權。我的經驗是大部分檔案工作者都知道并理解這一點,但我也聽說許多一年級的法律專業的學生對此頗為不解。
檔案館中的實際所有權和版權至少存在四種可能的形式。第一種可能性是,檔案館對該物品既沒有實際所有權又沒有版權,該物品僅僅是寄存。這種情況下,檔案館對物品采取的所有行為都要依據寄存協議,受到嚴格限制。
如果檔案館實際擁有實物,而且物品是通過從上級機構或捐贈、購買或其他途徑獲得的,那么知識產權應歸誰所有呢?在檔案館實際擁有實物的情況下還存在三種方式:檔案館可以擁有物品的知識產權,第三方可以擁有知識產權,或該物品屬于公共領域。根據不同的理論家的觀點,公共領域中物品的版權屬于公眾或不屬于任何人。
版權歸誰所有為什么這么重要呢?聯邦版權賦與版權所有人一些重要的權利。版權所有人擁有的權利中包括的特權有:對原件進行復制,向其他人分發拷貝(不論是出售或是租借),以享有版權的原件為基礎制作仿制品,某些時候還有展示或演出作品的權力。
很明顯,版權法對檔案館的運作有很大關系。我們向用戶“展示”館藏圖片,根據需求郵寄分發拷貝,有時還對館藏作品進行翻譯、編輯或出版。我們對于數字館藏的利用方式很容易被別人發現并引起關注。
那些希望從館藏中獲取利潤的檔案工作者要特別關注版權法。如果檔案館同時擁有實物及其版權,就可以自由地采用任何方式充分利用這些資料。同時擁有實物及其版權的檔案館實際上與出版社、軟件公司、電影制版廠這些將所有的版權作為業務的一部分的企業沒有不同。
如果檔案館擁有實物,而版權歸第三方所有該怎么辦?檔案館就不一定能夠輕松地從這些資料上獲取利潤。由于復制和分發都是版權所有人的特權,所以在制作和出售復制品的時候需要得到版權所有人的許可。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利用版權法中版權所有人特權的例外情況,特別是版權所有人不詳或無法查找的時候。但是幾乎所有的情況下,進行任何復制和分發的時候都必須不帶任何直接或間接性商業利益。從理論上講,為獲取利潤制作拷貝的作法是非法的,不但不能為機構獲得利潤,還有可能導致機構面臨民事或刑事處罰的危險。
版權所有人享有的普遍特權之中有一個重要的例外情況。依我的觀點看也是版權法中最不恰當的例外。通常,對版權所有人的各種限制,例如“正當使用”,規定了版權作品的拷貝數量或者保留該拷貝的期限。對版權所有人特權的其他限制來自格式限制,以及對有關文字、圖像資料和藝術品的各種規定。但是有一種例外不限制拷貝的數量、保存拷貝的期限和拷貝資料的格式。這種情況只適用于保存有未經發表資料的檔案館。這種例外情況允許檔案館和圖書館出于保存,或出于研究目的對保存/寄存在其他圖書館或檔案館的未經出版的作品進行整體拷貝。
議會為什么會同意由Julian Boyd代表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SAA)提出的這個例外情況的請求?該法案附帶的注釋中沒有解釋為什么國會在面對未經出版的資料時情愿忽視版權所有人的利益。而對出版資料方面的規定就沒有這種條款。
答案似乎是因為國會認為公眾在利用未出版檔案資料方面的利益的重要性大于版權所有人的利益。公眾閱讀未經出版的唯一資料非常重要,版權所有人的利益必須退居第二位。
公眾在公共領域中的利益
在公共領域中,公眾的利益方面的條款是最明確的。我們的檔案館中的許多資料都屬于公共領域。從今年開始,1933年以前去世的作家所著的所有未經出版的作品,以及1883年之前由匿名作者或團體作者生成的所有未經發表的作品都劃為公共領域,與所有聯邦政府所有作品(自動成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成為一類。公共領域內的作品沒有版權,版權所有人享有的特權,包括制作復制品、分發和展示的權力屬于所有的人。
有些人,包括國會女議員Mary Bono呼吁取消公共領域。他們不能理解為什么版權不能永遠持續。公共領域是美國版權系統存在的基礎。版權實質上就是一個平衡。公共賦予某一作品的作者利用該作品的有限的壟斷權,作為創作作品的一種回報,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壟斷權,則創作出的所有作品都屬于公共領域。人們擔憂的是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作者們就會停止創作。作為給予壟斷權的一種回報,公眾得到可以閱讀、研究和學習的新作品,包括書籍、電影、音樂和藝術。當壟斷期結束以后,公眾就能自由地使用和重復使用曾經有版權的作品。例如,迪斯尼電影《木偶奇遇記》在CarloCollodi的書美國版權到期后的一年之內問世,還有一些其他某著名電影,包括《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灰姑娘》,《巴黎圣姆院》,《愛麗絲漫游奇境》都是以屬于公共領域的作品為基礎的。先前的版權所有人不能控制作品復制的時間和方式,也不能反對公眾采用什么方式處理作品。
毫無疑問,把國家檔案館藏的大部分劃為公共領域對于此類資料的用戶和收藏資料的檔案館都是好事。現在檔案館可以考慮開發這些館藏,不用擔心是否侵犯了版權所有人的權力。
對公共領域版權采取部分版權控制
與版權所有人壟斷權力相比,許多檔案館更希望能對館藏資料的未來使用保留一種類似于部分版權控制的作法。因為許多博物館和某些檔案館實際擁有曾經有版權的作品,所以他們采用了這些部分版權控制的策略。我很欣賞Kathleen Butler的一篇文章,雖然文章的題目不是《如何利用圖片和數字復制品的版權控制公共領域中的藝術形象》。她在文章中寫到:“物品所有者通過控制對物品的實際利用,有機會并有權控制復制品的制作、使用和許可證的發放。”例如,博物館嚴禁拍照,或禁止使用三腳架照相機,以防止拍攝達到出版水平的照片。
根據藝術史學家Robert Barton的觀點,博物館允許利用公共領域資料進行復制的準則并不是從機構的教育和社會責任的角度出發,而是由于博物館希望從追逐利益的出版社那里獲取利潤,或者通過珍藏館藏保護機構的名譽。Barton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博物館就是監獄,圖片則是用來加強博物館個體形象的監獄犯人。”
除了通過增加對珍貴物品的利用規定控制其使用,有些博物館(和檔案館)還試圖壟斷館藏中屬于公共領域的珍貴物品的復制權。只有研究人員簽定了關于如何使用復制品的協議之后才能使用復制品。如果是在線環境,用戶通常都必須通過點擊的方式達成一份協議,遵守公共領域中圖像和文件的使用規定。個別極端情況下,獲得在線許可的簽約用戶在瀏覽網址之前要同意38條規定。用戶必須同意如果沒有允許,即使作品屬于公共領域,也不得將網址上查到的信息用作個人使用,或用于營利目的。如果沒有得到原件收藏機構的允許,該資料不得分發或復制,通常是版權所有人保留權力。用戶可以購買網址上的數字文件的拷貝,但如果用于商業用途、出版、展示或分發則需要得到許可。用Robert Barton的話來說,這些文件已經成了“監獄犯人”。
關于反對公共領域資料控制的法律爭論
人們出于幾個法律上的原因對公共領域物品的利用許可和物品復制協議存有疑慮。第一,現在有一種傾向認為那些不能屬于個人或團體的某些物品可以是我們共同的文件遺產的一部分。它們中的一部分屬于所有人。Joseph Sax曾寫過一本名為《文化精品中的公眾和私人權力》的非常有深度的書,他在書中寫到:“有些物品……是某個集體的組成部分,普通的私人使用會影響集體所有權。”Sax還認為,由于大型藝術作品部分屬于公眾,所以應要求私人收藏家周期性地把這些作品出租給公共機構,以便公眾能自由利用。
我們都熟悉為私有財產所有人自由利益而制定的分區法規(zoninglaw)。歷史保護方面的法規可以限制建筑物的改動方式,有些地方,例如加利福尼亞,有些財產的所有人必須允許公眾使用海灘,即使這意味著要穿過私人財產。實際上,公共享有歷史建筑或海灘的部分所有權。我們檔案館中的文件可能也是如此。這些文件屬于檔案館,但同時也屬于社會,社會可以有權對公眾開放這些作品。
第二,如果公眾擁有公共領域作品的版權(與沒有人擁有這種版權相對應),那么公眾就可以合法地利用并拷貝屬于公共領域的物品。在Reid與Creative Non-Violence委員會(CCNV)之間發生的訴訟中,法庭裁定CCNV必須允許John Reid利用一座雕塑以便制作一個復制品。Reid曾經為CCNV制作了這個雕塑,并保留了作品的版權。法庭稱如果版權所有人擁有版權,而他或她又不能利用唯一的原件進行復制,就會對所有人不利。這樣,有人就會認為可以對該裁決進行邏輯擴展:由于作品的實際版權歸公眾所有,所以公眾就應自由復制機構中屬于公共領域的作品,而不用考慮任何的利用限制。
第三,有些法律方面的學者認為在合同法中重復版權保護的作法值得懷疑。版權法中的“優先購買”條款稱:對于“與版權普遍范圍中之任何特殊權力相等的權力”,聯邦版權法比其他任何國家法律優先適用。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在法庭上得到驗證)是關于檔案館是否可以通過國家合同法重建版權所有人特權。
最后,許多檔案館把版權須知印在公共領域作品復制件上。但是,在Bridgemanv. Corel,法庭裁定公共領域作品的精確照片副本本身不具有版權,因為這些不是原件。制作精確照片副本可能要求很高的技術并付出很大的努力,但僅僅這樣做還足以保證版權的保護。在這些復制品上印上明顯的版權須知可能會使主辦機構面臨某種風險。其中包括,如果所印版權有誤就是犯罪行為,并處以2500美元的罰款。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檔案館被處罰過,但總的來說遵守法律是安全的。
檔案原則和公共領域資料的管理
限制利用館藏中公共領域作品的規定有時是無效的,原因包括:文化遺產物品利用方面的法律規定,公眾享有的復制擁有版權物品的權力、優先購買的權力和對欺騙性版權須知的批評。設立以版權為基礎的合理原則的根本依據就是以上幾個原因。請記住,公眾賦予作者在某個時段的壟斷權力,在這個期間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作品,而時間截止之后作品就歸公眾所有了。博物館(和檔案館)希望長期控制作品使用權的作法實際上就是表示作品的管理工作比創作還要重要。社會只需暫時賦予創作人有限的壟斷權力,但檔案館的利益需要得到永遠的保護。但我們真的相信所有權比創作更值得回報嗎?
我們還應謹記檔案館的崇高目標。我們的任務是盡最大努力保管好職責范圍內的需要保護的物品。我們有責任將它們保存完好并交給子孫后代。我們還有責任向公眾傳播有關我們館藏內容的知識。正如JohnFleckner所教導的那樣,我們通過向社會開放歷史性文件來維持一個公正的社會,保護公民的權力,對專制政府發揮檢查作用,并(以單獨或集體的方式)保證我們對歷史的所有權。如果檔案館成了個人或機構進行資產開發的機構,那么會出現什么情況?
有人曾告訴我,最近傳聞一些非常有名的研究性大學將只允許本校的教工和學生利用檔案館和原稿部門保存的資料。盡管這種作法在五十年以前很普遍,現在大部分人都拒絕這種理念。這種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把檔案館看成一個值錢的大學資產,應該用來為大學謀福利,而不是大學應具備的公益性。這種關于檔案館商品化的建議在檔案原則中有將近五十年的歷史。
控制使用時遇到的倫理和實際問題
除了法律和原則之外,我們對捐獻者負有的倫理責任也是為什么要避免對公共領域作品利用制定太多限制的原因。在擔任原稿管理人期間,我用了大量時間說服人們向我所工作的檔案館捐獻個人檔案及其版權。我的理由是這種捐獻可以支持學術和研究工作,并符合社會利益。我從來沒有與他們討論過捐獻品潛在的金錢價值,也沒有表示過我們搜集文件的目的是為了從他們那里為自己掙得資金收入。如果資料是購買來的就不會出現這種問題。但對于那些捐獻的資料,如果利用捐獻品中的資料進行復制用于銷售,那么根據捐獻的權限,捐獻人有權了解這方面的情況。
最后,對于實際情況,對公眾領域復制品進行壟斷的努力似乎不會成功。例如,即使禁止使用公共領域內作品復制件進行復制的規定有效,這種合同也只發生在機構和要求進行復制的最初用戶之間。如果一件復制品到了第三方手中,他們也可以對它進行復制,而且不會受到任何懲罰。檔案館所能做的是采取措施限制進行非法復制的個人(如果能找出這個人的話)。有些機構正尋求使用水印、加密和其他技術手段限制使用經數字化之后的資源。這些解決方法也不是十全十美,仍然要求從檔案館的角度出發采取法律手段。而且如果檔案館將那些通過廉價掃描設備就可以輕易數字化的作品的復制件的硬拷貝出售,那么這些方法就很容易被破壞。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極其明顯的。試圖通過開發我們實際掌握的公共領域作品獲取大額利潤的方法是不會成功的。這些做法是對版權生成者和公眾這兩者利益之間獲得版權平衡的一種諷刺。做法忽視了公眾在館藏方面的所有權利益,可能在法律上行不通,這要取決于實施的情況,并有可能構成犯罪。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公共文件,檔案館需要更多的資金。我們怎樣做才能避免“捧著金飯碗要飯吃”的局面?如果檔案館不擁有館藏品的部分版權,又如何從中獲取資金呢?
正當的資金生成
關于檔案館如何從館藏中正當獲取資金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在對公共領域資料進行拷貝的時候,我希望所有的檔案館盡可能在市場能夠承受和工作職責(與捐獻人達成明確協議)允許的情況下收費。不能對復制件的進一步使用增加限制,否則就可能有人會以低于檔案館收費標準提供復制件。但此處我還再提醒一句,當涉及公眾領域時,“我們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他們的工作人員”,你擁有的唯一權力是出售文件的復制件。所以對復制的收費標準也應心安理得。
芝加哥研究圖書館中心的Bernard Reilly對我的第二種建議有異議。Reilly提出圖書館和博物館應更類似于Enron公司。我建議檔案館也應更類似于Enron公司,但我的理由與他稍有不同。我現在決不是在講檔案館為了解決財政難題而進行秘密結算、股票操縱或違法銷毀文件。
現在請大家想一想Enron公司從事何種生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和商業公司之一,但它并沒有任何油田、電廠或其他能源資源。從最初的管道公司開始,Enron發展神速,它停止了實際資料資產方面的貿易,轉而經營資源所有權,后來又從事尚未發現的資源期貨價值的業務。Enron倒閉的時候僅僅是一家能源公司,而不是什么經營能源期貨、頻帶寬甚至天氣的投資集團。資產都是由其他人擁有的。而Enron只靠銷售和使用它掌握的有關這些實際資產的信息致富。
我希望檔案館在這方面的類似情況是很明顯的。我們并不是完全擁有檔案館中所有的實際公共領域物品。當這些物品還屬于私人財產時,它們同時也是公共商品,公眾與之有利害關系。我們如何利用既不完全擁有,也不能壟斷的物品獲得利潤?答案就是銷售,像Enron公司一樣,我們靠的不同館藏的實際資產,而是我們掌握的文件方面的信息。人們之所以從檔案館的網址上訂購公共領域作品的復制件不是因為我們利用許可證協議限制這些作品的使用,而是我們提供了用戶在其他地方不能找到的信息和服務,這種信息和服務可能是完整準確的元數據、內容條款、真實性的保證、能在未來提供資源的承諾,或是某種能夠使所需作品的尋找、訂購和接收更為便利的系統。
Hewlett-Packard的一位名叫Alan Karp的研究科學人員最近發表了一篇頗為引人關注的文章,題目是Communi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他在文章中稱,文字工業應更加類似于色情工業。色情網址(通常要收費)是訪問率最高的網址之一,盡管單個形象很容易被拷貝并在其他地方免費使用。他建議,色情網址的成功是因為提供了附加值。它們有吸引人的界面,而且由于在設備方面的實際投入很多,所以性能很好,另外還有貼近用戶需求的很容易訪問的元數據。Karp稱:“增加值使用戶更有理由從你那里而不是從你的供應商那里直接購買。”
關于銷售方面的增加值服務的作用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最近設立了一個網址以紀念館藏量達到1700萬冊。第1700萬冊書是1865年和1866年在華盛頓特區出版的由Alexander Gardner所著的《戰爭圖片速寫錄》(Photographic Sketch Book of the War)。網址的其中一頁專門刊登整版插圖23,《林肯總統在Antietam戰場》。其中有照片,還標明了拍攝人和拍攝過程,并提供了其他有價值的信息。網址上沒有給出如何訂購照片拷貝,但是細心的利用者如果查看剩余網址就會了解,未指定尺寸照片的沖印費用僅為20美元。
紐約時報網上書店也出現了同樣的照片。照片的名稱是《林肯和部隊在Antietam戰場(原文如此),1862年》Alexander Gardner被稱為攝影師。照片沒有附文字,也沒有表明它是來自一本書,也沒有原件照片拍攝過程的信息。但在這里訂購的渠道很方便:未加框的照片售價為195至495美元,加框的照片價格是340至745美元。
你可能會問,康奈爾網站、國會圖書館的美國記憶網站及萬維網上的幾個很容易找到的網站上就有質量很高的數字拷貝,為什么人們還會花大價錢購買?而且這些網站還可以提供價錢低得多的照片。
原來紐約時報提供了歷史檔案館所沒有的附加值服務:便利的搜索、訂購、照片框的在線樣本等等。紐約時報的經營模式是它提供的服務,而不是對所提供內容的壟斷。最近對數字文件內容發展企業模式的研究表明,文化遺產機構為了能夠在將來成功發布在線數字文化內容,他們需要在產品的銷售方面開發更為商業化的方法,特別要了解用戶需求和需要。另外還有一個好處,檔案館向其用戶出售的所有增加值服務的確都屬于檔案館,人們可以采取一些保護措施,這是公共領域內的文件所不能享受的。
Enron公司、色情網站和紐約時報是未來檔案資產管理系統應模仿的模式。檔案館中的實際資產不是館藏,而是受過訓練的檔案專業人員的技能、才智、知識和能力。這才是檔案館需要促銷的檔案資產。
(陳慧涵摘自《外國檔案工作動態》 譯:李紅)
(Peter B.Hirtle是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教育、研究和信息服務部主任,曾擔任康奈爾大學數字文件匯集部的主任。同時,Hirtle先生還是D-Lib雜志的副主編。他是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2003-2004年第58任年度主席。)
編者的話:
在2003年8月21日于加利福尼亞洛杉磯召開的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年會的開幕式全體會議上,PeterB.Hiltle主席發表了這篇講話。
今年4月,華盛頓郵報報道,Bob Woodward和CarlBemstein的文章被以5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給了德克薩斯大學的Harry Ransom人文研究中心。“水門事件”丑聞的大部分都是這兩個人披露的。華盛頓郵報中的文章稱還有其他一些文章以大約相同的價格出售,其中,SusanSontag的文章賣了110萬美元,Francis Crick的文章賣了130萬美元,Zapruder拍攝的肯尼迪遇刺的膠片賣了1600萬美元,溫斯頓?丘吉爾的部分文章賣了1840萬美元。其實,報道中可以引用的收購方面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2000年美國政府花了1800萬美元購買里查德?尼克松的文章,或者Sotheby向國會圖書館提出以2000萬美元出售馬丁路德?金的部分文章,經鑒定,這些文章估價為3000萬美元。
對所有的檔案工作者來說,檔案文件可以具有經濟價值并不為奇。我們保管的文件對歷史、文化和價值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如果在e-Bay或拍賣所,這些文件也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我聽說,就在我工作的康奈爾大學,據評估圖書館是大學擁有的唯一最大規模的資產。由于康奈爾大學擁有7000萬原稿文件,比如林肯《格底斯堡演講》手跡、James Joyce的《尤里西斯》的部分手稿,圖書館的大部分價值就在于檔案和手稿文匯集,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簡而言之,檔案和手稿庫房中管理著價值上億美元的資產。然而檔案館一直資金不足。許多檔案館是“捧著金飯碗要飯”:我們有價值百萬的資本資產,卻沒錢雇用員工、維護設備或支付公用事業費用。
由于需要資金,同時又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同時也是值得稱贊的原因)不愿意出售資產,所以許多檔案館就尋求從管理的檔案資料中獲取收入。檔案資料復制品的出售以及為資料用于商業目的頒發許可證正成為檔案館越來越重要的收入來源。
檔案館尋求通過館藏獲取資金的方式實際上是在步博物館之后塵。長期以來博物館一直利用為各種項目頒發許可增加收入。對于某些博物館來說,為其館藏藝術品頒發許可證已經成為資金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可以用來支持教育和管理項目,并把知識產權管理作為一項主要的行政任務。
把檔案館藏數字化也使人們更加注意其可能存在的經濟價值。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數字化的內容可能會帶來資金收益。例如,Lesley Ellen Harris是專門為博物館和圖書館撰寫知識產權問題的律師,他把數字資產看成是“二十一世紀的貨幣”。大多數的檔案工作者都知道商業數字化照片匯集,比如在Corbis,Getty Images和紐約新聞日報上刊登的照片,他們想了解通過利用自己的館藏是否可以和產生類似的經濟收入。很明顯,人們把檔案館藏看成經濟資產的觀點正日益加深。我們也認識到,即使檔案館中最不引人注目的文章片斷,如果我們想將其出售都可以從eBay那里獲得收益。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希望通過數字化可以把固定的資本資產轉化成流動的現金。
我相信,對檔案館藏的商業開發可以采取一種有利于整體檔案工作責任的方式,即將過去的資源變為未來的可用之材。然而,理想中的結果并不是注定能實現的。現實的風險是,對檔案館藏的經濟開發可能會與我們的中心原則和價值觀發生沖突。
所以,在今天上午的會上,我準備和大家討論一下我們擁有的檔案館藏所有權的本質,以及它可能對館藏開發產生的影響。我們經常聽檔案工作者談論保護“我們的東西”,但文獻資料作為檔案的本質是什么?
諸位大都知道我對知識產權問題非常感興趣。我們可以通過知識產權法的一些概念,特別是關于公眾領域方面的觀念了解擁有檔案文件的含義是什么。我想讓大家明白,對公共領域資料的擁有與擁有一輛車或一所房屋的概念是不同的。實際上,對于我們檔案館中的資料,我們并不是擁有全部,有些部分是歸公眾所有的,如果我們想對這些資料采取類似于壟斷的作法,那么就是在危害公共。因而,人們經常在Archives & Archivists listserv上看到的關于使用“我們的東西”的報怨,或是要求對數字圖像的使用采用水印或加密技術的建議都屬于錯誤認識。
為了尊重公眾在檔案資料方面的利益,我們在制定許可證體制的時候要特別謹慎。我認為,如果檔案工作者能在尋求經濟收益的同時堅持我們基本的價值觀,同時尊重公眾在公共領域資料方面的利益,就能夠避免許多博物館因為試圖壟斷和控制館藏而招至的譴責。
知識產權法和所有權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知識產權法關于檔案文件所有權的規定是什么。第一,版權法在某件物品的實際所有權和其版權之間劃分了明顯的界限。一個人掌握一封信、一張照片或膠片并不意味著他擁有其版權。我的經驗是大部分檔案工作者都知道并理解這一點,但我也聽說許多一年級的法律專業的學生對此頗為不解。
檔案館中的實際所有權和版權至少存在四種可能的形式。第一種可能性是,檔案館對該物品既沒有實際所有權又沒有版權,該物品僅僅是寄存。這種情況下,檔案館對物品采取的所有行為都要依據寄存協議,受到嚴格限制。
如果檔案館實際擁有實物,而且物品是通過從上級機構或捐贈、購買或其他途徑獲得的,那么知識產權應歸誰所有呢?在檔案館實際擁有實物的情況下還存在三種方式:檔案館可以擁有物品的知識產權,第三方可以擁有知識產權,或該物品屬于公共領域。根據不同的理論家的觀點,公共領域中物品的版權屬于公眾或不屬于任何人。
版權歸誰所有為什么這么重要呢?聯邦版權賦與版權所有人一些重要的權利。版權所有人擁有的權利中包括的特權有:對原件進行復制,向其他人分發拷貝(不論是出售或是租借),以享有版權的原件為基礎制作仿制品,某些時候還有展示或演出作品的權力。
很明顯,版權法對檔案館的運作有很大關系。我們向用戶“展示”館藏圖片,根據需求郵寄分發拷貝,有時還對館藏作品進行翻譯、編輯或出版。我們對于數字館藏的利用方式很容易被別人發現并引起關注。
那些希望從館藏中獲取利潤的檔案工作者要特別關注版權法。如果檔案館同時擁有實物及其版權,就可以自由地采用任何方式充分利用這些資料。同時擁有實物及其版權的檔案館實際上與出版社、軟件公司、電影制版廠這些將所有的版權作為業務的一部分的企業沒有不同。
如果檔案館擁有實物,而版權歸第三方所有該怎么辦?檔案館就不一定能夠輕松地從這些資料上獲取利潤。由于復制和分發都是版權所有人的特權,所以在制作和出售復制品的時候需要得到版權所有人的許可。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利用版權法中版權所有人特權的例外情況,特別是版權所有人不詳或無法查找的時候。但是幾乎所有的情況下,進行任何復制和分發的時候都必須不帶任何直接或間接性商業利益。從理論上講,為獲取利潤制作拷貝的作法是非法的,不但不能為機構獲得利潤,還有可能導致機構面臨民事或刑事處罰的危險。
版權所有人享有的普遍特權之中有一個重要的例外情況。依我的觀點看也是版權法中最不恰當的例外。通常,對版權所有人的各種限制,例如“正當使用”,規定了版權作品的拷貝數量或者保留該拷貝的期限。對版權所有人特權的其他限制來自格式限制,以及對有關文字、圖像資料和藝術品的各種規定。但是有一種例外不限制拷貝的數量、保存拷貝的期限和拷貝資料的格式。這種情況只適用于保存有未經發表資料的檔案館。這種例外情況允許檔案館和圖書館出于保存,或出于研究目的對保存/寄存在其他圖書館或檔案館的未經出版的作品進行整體拷貝。
議會為什么會同意由Julian Boyd代表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SAA)提出的這個例外情況的請求?該法案附帶的注釋中沒有解釋為什么國會在面對未經出版的資料時情愿忽視版權所有人的利益。而對出版資料方面的規定就沒有這種條款。
答案似乎是因為國會認為公眾在利用未出版檔案資料方面的利益的重要性大于版權所有人的利益。公眾閱讀未經出版的唯一資料非常重要,版權所有人的利益必須退居第二位。
公眾在公共領域中的利益
在公共領域中,公眾的利益方面的條款是最明確的。我們的檔案館中的許多資料都屬于公共領域。從今年開始,1933年以前去世的作家所著的所有未經出版的作品,以及1883年之前由匿名作者或團體作者生成的所有未經發表的作品都劃為公共領域,與所有聯邦政府所有作品(自動成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成為一類。公共領域內的作品沒有版權,版權所有人享有的特權,包括制作復制品、分發和展示的權力屬于所有的人。
有些人,包括國會女議員Mary Bono呼吁取消公共領域。他們不能理解為什么版權不能永遠持續。公共領域是美國版權系統存在的基礎。版權實質上就是一個平衡。公共賦予某一作品的作者利用該作品的有限的壟斷權,作為創作作品的一種回報,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壟斷權,則創作出的所有作品都屬于公共領域。人們擔憂的是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作者們就會停止創作。作為給予壟斷權的一種回報,公眾得到可以閱讀、研究和學習的新作品,包括書籍、電影、音樂和藝術。當壟斷期結束以后,公眾就能自由地使用和重復使用曾經有版權的作品。例如,迪斯尼電影《木偶奇遇記》在CarloCollodi的書美國版權到期后的一年之內問世,還有一些其他某著名電影,包括《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灰姑娘》,《巴黎圣姆院》,《愛麗絲漫游奇境》都是以屬于公共領域的作品為基礎的。先前的版權所有人不能控制作品復制的時間和方式,也不能反對公眾采用什么方式處理作品。
毫無疑問,把國家檔案館藏的大部分劃為公共領域對于此類資料的用戶和收藏資料的檔案館都是好事。現在檔案館可以考慮開發這些館藏,不用擔心是否侵犯了版權所有人的權力。
對公共領域版權采取部分版權控制
與版權所有人壟斷權力相比,許多檔案館更希望能對館藏資料的未來使用保留一種類似于部分版權控制的作法。因為許多博物館和某些檔案館實際擁有曾經有版權的作品,所以他們采用了這些部分版權控制的策略。我很欣賞Kathleen Butler的一篇文章,雖然文章的題目不是《如何利用圖片和數字復制品的版權控制公共領域中的藝術形象》。她在文章中寫到:“物品所有者通過控制對物品的實際利用,有機會并有權控制復制品的制作、使用和許可證的發放。”例如,博物館嚴禁拍照,或禁止使用三腳架照相機,以防止拍攝達到出版水平的照片。
根據藝術史學家Robert Barton的觀點,博物館允許利用公共領域資料進行復制的準則并不是從機構的教育和社會責任的角度出發,而是由于博物館希望從追逐利益的出版社那里獲取利潤,或者通過珍藏館藏保護機構的名譽。Barton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博物館就是監獄,圖片則是用來加強博物館個體形象的監獄犯人。”
除了通過增加對珍貴物品的利用規定控制其使用,有些博物館(和檔案館)還試圖壟斷館藏中屬于公共領域的珍貴物品的復制權。只有研究人員簽定了關于如何使用復制品的協議之后才能使用復制品。如果是在線環境,用戶通常都必須通過點擊的方式達成一份協議,遵守公共領域中圖像和文件的使用規定。個別極端情況下,獲得在線許可的簽約用戶在瀏覽網址之前要同意38條規定。用戶必須同意如果沒有允許,即使作品屬于公共領域,也不得將網址上查到的信息用作個人使用,或用于營利目的。如果沒有得到原件收藏機構的允許,該資料不得分發或復制,通常是版權所有人保留權力。用戶可以購買網址上的數字文件的拷貝,但如果用于商業用途、出版、展示或分發則需要得到許可。用Robert Barton的話來說,這些文件已經成了“監獄犯人”。
關于反對公共領域資料控制的法律爭論
人們出于幾個法律上的原因對公共領域物品的利用許可和物品復制協議存有疑慮。第一,現在有一種傾向認為那些不能屬于個人或團體的某些物品可以是我們共同的文件遺產的一部分。它們中的一部分屬于所有人。Joseph Sax曾寫過一本名為《文化精品中的公眾和私人權力》的非常有深度的書,他在書中寫到:“有些物品……是某個集體的組成部分,普通的私人使用會影響集體所有權。”Sax還認為,由于大型藝術作品部分屬于公眾,所以應要求私人收藏家周期性地把這些作品出租給公共機構,以便公眾能自由利用。
我們都熟悉為私有財產所有人自由利益而制定的分區法規(zoninglaw)。歷史保護方面的法規可以限制建筑物的改動方式,有些地方,例如加利福尼亞,有些財產的所有人必須允許公眾使用海灘,即使這意味著要穿過私人財產。實際上,公共享有歷史建筑或海灘的部分所有權。我們檔案館中的文件可能也是如此。這些文件屬于檔案館,但同時也屬于社會,社會可以有權對公眾開放這些作品。
第二,如果公眾擁有公共領域作品的版權(與沒有人擁有這種版權相對應),那么公眾就可以合法地利用并拷貝屬于公共領域的物品。在Reid與Creative Non-Violence委員會(CCNV)之間發生的訴訟中,法庭裁定CCNV必須允許John Reid利用一座雕塑以便制作一個復制品。Reid曾經為CCNV制作了這個雕塑,并保留了作品的版權。法庭稱如果版權所有人擁有版權,而他或她又不能利用唯一的原件進行復制,就會對所有人不利。這樣,有人就會認為可以對該裁決進行邏輯擴展:由于作品的實際版權歸公眾所有,所以公眾就應自由復制機構中屬于公共領域的作品,而不用考慮任何的利用限制。
第三,有些法律方面的學者認為在合同法中重復版權保護的作法值得懷疑。版權法中的“優先購買”條款稱:對于“與版權普遍范圍中之任何特殊權力相等的權力”,聯邦版權法比其他任何國家法律優先適用。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在法庭上得到驗證)是關于檔案館是否可以通過國家合同法重建版權所有人特權。
最后,許多檔案館把版權須知印在公共領域作品復制件上。但是,在Bridgemanv. Corel,法庭裁定公共領域作品的精確照片副本本身不具有版權,因為這些不是原件。制作精確照片副本可能要求很高的技術并付出很大的努力,但僅僅這樣做還足以保證版權的保護。在這些復制品上印上明顯的版權須知可能會使主辦機構面臨某種風險。其中包括,如果所印版權有誤就是犯罪行為,并處以2500美元的罰款。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檔案館被處罰過,但總的來說遵守法律是安全的。
檔案原則和公共領域資料的管理
限制利用館藏中公共領域作品的規定有時是無效的,原因包括:文化遺產物品利用方面的法律規定,公眾享有的復制擁有版權物品的權力、優先購買的權力和對欺騙性版權須知的批評。設立以版權為基礎的合理原則的根本依據就是以上幾個原因。請記住,公眾賦予作者在某個時段的壟斷權力,在這個期間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作品,而時間截止之后作品就歸公眾所有了。博物館(和檔案館)希望長期控制作品使用權的作法實際上就是表示作品的管理工作比創作還要重要。社會只需暫時賦予創作人有限的壟斷權力,但檔案館的利益需要得到永遠的保護。但我們真的相信所有權比創作更值得回報嗎?
我們還應謹記檔案館的崇高目標。我們的任務是盡最大努力保管好職責范圍內的需要保護的物品。我們有責任將它們保存完好并交給子孫后代。我們還有責任向公眾傳播有關我們館藏內容的知識。正如JohnFleckner所教導的那樣,我們通過向社會開放歷史性文件來維持一個公正的社會,保護公民的權力,對專制政府發揮檢查作用,并(以單獨或集體的方式)保證我們對歷史的所有權。如果檔案館成了個人或機構進行資產開發的機構,那么會出現什么情況?
有人曾告訴我,最近傳聞一些非常有名的研究性大學將只允許本校的教工和學生利用檔案館和原稿部門保存的資料。盡管這種作法在五十年以前很普遍,現在大部分人都拒絕這種理念。這種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把檔案館看成一個值錢的大學資產,應該用來為大學謀福利,而不是大學應具備的公益性。這種關于檔案館商品化的建議在檔案原則中有將近五十年的歷史。
控制使用時遇到的倫理和實際問題
除了法律和原則之外,我們對捐獻者負有的倫理責任也是為什么要避免對公共領域作品利用制定太多限制的原因。在擔任原稿管理人期間,我用了大量時間說服人們向我所工作的檔案館捐獻個人檔案及其版權。我的理由是這種捐獻可以支持學術和研究工作,并符合社會利益。我從來沒有與他們討論過捐獻品潛在的金錢價值,也沒有表示過我們搜集文件的目的是為了從他們那里為自己掙得資金收入。如果資料是購買來的就不會出現這種問題。但對于那些捐獻的資料,如果利用捐獻品中的資料進行復制用于銷售,那么根據捐獻的權限,捐獻人有權了解這方面的情況。
最后,對于實際情況,對公眾領域復制品進行壟斷的努力似乎不會成功。例如,即使禁止使用公共領域內作品復制件進行復制的規定有效,這種合同也只發生在機構和要求進行復制的最初用戶之間。如果一件復制品到了第三方手中,他們也可以對它進行復制,而且不會受到任何懲罰。檔案館所能做的是采取措施限制進行非法復制的個人(如果能找出這個人的話)。有些機構正尋求使用水印、加密和其他技術手段限制使用經數字化之后的資源。這些解決方法也不是十全十美,仍然要求從檔案館的角度出發采取法律手段。而且如果檔案館將那些通過廉價掃描設備就可以輕易數字化的作品的復制件的硬拷貝出售,那么這些方法就很容易被破壞。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極其明顯的。試圖通過開發我們實際掌握的公共領域作品獲取大額利潤的方法是不會成功的。這些做法是對版權生成者和公眾這兩者利益之間獲得版權平衡的一種諷刺。做法忽視了公眾在館藏方面的所有權利益,可能在法律上行不通,這要取決于實施的情況,并有可能構成犯罪。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公共文件,檔案館需要更多的資金。我們怎樣做才能避免“捧著金飯碗要飯吃”的局面?如果檔案館不擁有館藏品的部分版權,又如何從中獲取資金呢?
正當的資金生成
關于檔案館如何從館藏中正當獲取資金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在對公共領域資料進行拷貝的時候,我希望所有的檔案館盡可能在市場能夠承受和工作職責(與捐獻人達成明確協議)允許的情況下收費。不能對復制件的進一步使用增加限制,否則就可能有人會以低于檔案館收費標準提供復制件。但此處我還再提醒一句,當涉及公眾領域時,“我們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他們的工作人員”,你擁有的唯一權力是出售文件的復制件。所以對復制的收費標準也應心安理得。
芝加哥研究圖書館中心的Bernard Reilly對我的第二種建議有異議。Reilly提出圖書館和博物館應更類似于Enron公司。我建議檔案館也應更類似于Enron公司,但我的理由與他稍有不同。我現在決不是在講檔案館為了解決財政難題而進行秘密結算、股票操縱或違法銷毀文件。
現在請大家想一想Enron公司從事何種生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和商業公司之一,但它并沒有任何油田、電廠或其他能源資源。從最初的管道公司開始,Enron發展神速,它停止了實際資料資產方面的貿易,轉而經營資源所有權,后來又從事尚未發現的資源期貨價值的業務。Enron倒閉的時候僅僅是一家能源公司,而不是什么經營能源期貨、頻帶寬甚至天氣的投資集團。資產都是由其他人擁有的。而Enron只靠銷售和使用它掌握的有關這些實際資產的信息致富。
我希望檔案館在這方面的類似情況是很明顯的。我們并不是完全擁有檔案館中所有的實際公共領域物品。當這些物品還屬于私人財產時,它們同時也是公共商品,公眾與之有利害關系。我們如何利用既不完全擁有,也不能壟斷的物品獲得利潤?答案就是銷售,像Enron公司一樣,我們靠的不同館藏的實際資產,而是我們掌握的文件方面的信息。人們之所以從檔案館的網址上訂購公共領域作品的復制件不是因為我們利用許可證協議限制這些作品的使用,而是我們提供了用戶在其他地方不能找到的信息和服務,這種信息和服務可能是完整準確的元數據、內容條款、真實性的保證、能在未來提供資源的承諾,或是某種能夠使所需作品的尋找、訂購和接收更為便利的系統。
Hewlett-Packard的一位名叫Alan Karp的研究科學人員最近發表了一篇頗為引人關注的文章,題目是Communi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他在文章中稱,文字工業應更加類似于色情工業。色情網址(通常要收費)是訪問率最高的網址之一,盡管單個形象很容易被拷貝并在其他地方免費使用。他建議,色情網址的成功是因為提供了附加值。它們有吸引人的界面,而且由于在設備方面的實際投入很多,所以性能很好,另外還有貼近用戶需求的很容易訪問的元數據。Karp稱:“增加值使用戶更有理由從你那里而不是從你的供應商那里直接購買。”
關于銷售方面的增加值服務的作用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最近設立了一個網址以紀念館藏量達到1700萬冊。第1700萬冊書是1865年和1866年在華盛頓特區出版的由Alexander Gardner所著的《戰爭圖片速寫錄》(Photographic Sketch Book of the War)。網址的其中一頁專門刊登整版插圖23,《林肯總統在Antietam戰場》。其中有照片,還標明了拍攝人和拍攝過程,并提供了其他有價值的信息。網址上沒有給出如何訂購照片拷貝,但是細心的利用者如果查看剩余網址就會了解,未指定尺寸照片的沖印費用僅為20美元。
紐約時報網上書店也出現了同樣的照片。照片的名稱是《林肯和部隊在Antietam戰場(原文如此),1862年》Alexander Gardner被稱為攝影師。照片沒有附文字,也沒有表明它是來自一本書,也沒有原件照片拍攝過程的信息。但在這里訂購的渠道很方便:未加框的照片售價為195至495美元,加框的照片價格是340至745美元。
你可能會問,康奈爾網站、國會圖書館的美國記憶網站及萬維網上的幾個很容易找到的網站上就有質量很高的數字拷貝,為什么人們還會花大價錢購買?而且這些網站還可以提供價錢低得多的照片。
原來紐約時報提供了歷史檔案館所沒有的附加值服務:便利的搜索、訂購、照片框的在線樣本等等。紐約時報的經營模式是它提供的服務,而不是對所提供內容的壟斷。最近對數字文件內容發展企業模式的研究表明,文化遺產機構為了能夠在將來成功發布在線數字文化內容,他們需要在產品的銷售方面開發更為商業化的方法,特別要了解用戶需求和需要。另外還有一個好處,檔案館向其用戶出售的所有增加值服務的確都屬于檔案館,人們可以采取一些保護措施,這是公共領域內的文件所不能享受的。
Enron公司、色情網站和紐約時報是未來檔案資產管理系統應模仿的模式。檔案館中的實際資產不是館藏,而是受過訓練的檔案專業人員的技能、才智、知識和能力。這才是檔案館需要促銷的檔案資產。
(陳慧涵摘自《外國檔案工作動態》 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