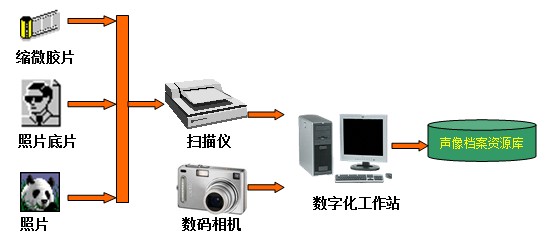胡鴻杰同志在(檔案學通訊)2004年第4期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以研究領域與研究態度為例指出應當改進我們的檔案學研究,讀畢甚有同感。近年來我國的檔案學理論研究較為活躍,新觀點、新思想不斷涌現,為推動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與檔案工作實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經幾年的觀察,不難發現,以往檔案學理論研究中的不足除存在研究領域與研究態度方面的問題外,還有研究的出發點、研究視角與方法等問題,我們的檔案學理論研究的確應當改進。
一、檔案學理論研究應從我國檔案實際出發
檔案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是要解決研究對象的問題。顧名思義,檔案學理論研究不管是研究檔案(文件)的運動規律,還是研究檔案的價值,都要以檔案為對象,而我國的檔案學理論研究則應以我國關于檔案的概念為出發點。這一問題看似理所當然,但要做到準確運用概念卻不那么容易。其原因之一是我國檔案概念的外延較大。以法定檔案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檔案法》)指出:“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這種歷史紀錄,不論存放地點均視為檔案,它可以存放在檔案館或檔案室里,甚至也可以存放在家庭和個人手中;也不論保管時限均視為檔案,它可以是永久保管或長達50年長期保管的,甚至也可以是只保管15年以下(當然也包括只保管3-5年)短期保管的。檔案概念外延如此之大,使我們在研究中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對象時往往難以把握。其原因之二是受研究者視角的局限。我國檔案工作者的職業特點是分工細但缺乏綜合,例如,在機關、企事業單位中從事檔案管理的同志不一定熟悉檔案館的具體業務與要求,在學校講授文書檔案管理學課程的同志不一定對科技檔案管理學有很系統深入的研究。由于對檔案工作業務(包括檔案館與檔案室的)與檔案學學科內容缺乏整體的把握,致使在理論研究中缺乏宏觀思考,往往局限于個人從事本單位的管理對象和教學內容的視野。由上述原因所致,使以往的檔案學理論研究往往帶有片面性,其研究成果雖冠以“檔案”名義,但實則與我國的檔案概念多少存在著差距。例如在關于文件運動規律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認為:文件運動規律的三大理論是檔案學理論中最基本的理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文件運動的線性特征,全宗理論是文件運動的群體特征,文件價值理論是文件運動的動力特征。應該說研究者的這種探討精神是可貴的,研究也是有成果的,能站在一個較高層面上進行綜合思考。然而,如果站在檔案整體的高度來看,不免令人產生疑惑,它是否為建立在我國檔案概念基礎上的檔案(文件)運動的普遍規律,例如它對檔案館以外的檔案是否適用?筆者以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全宗理論、文件價值理論所體現的運動特征對檔案館的檔案是適用的,但對我國廣大企事業單位與機關檔案室(尤其是沒有進館任務者)的檔案是不完全適用或不適用的,因為這些單位檔案文件的運動既不是按全宗特征來運動的,也不是都遵循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運動的。這些單位文件的每次歸檔(運動)只是全宗構成的一部分,而且運動階段也僅到檔案室,暫存和永久保存場所是合而為一的。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全宗理論、文件價值理論這些在國外形成的檔案學經典理論為什么用以說明中國的檔案文件運動規律顯得針對性不很強呢?答案只有一個,由于各國關于檔案概念的不同所致。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最早出現在美國,當時為了解決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累的大量文件致使保管費用過高的問題,需要組建文件中心或中間檔案館暫存。在美國是把經挑選進館研究保存的文件才稱為檔案的,因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對類似美國定義檔案概念的國家是適用的。再如全宗理論,它主要是檔案館的整理理論,其產生背景是當時為糾正法國國家檔案館單純按事由原則整理封建政權遺留檔案帶來的混亂,并不是針對基層單位檔案整理的。而在我國關于檔案的概念與外國不相同,檔案的范疇不僅包括檔案館的檔案,也包括基層檔案機構的檔案;不僅有文書檔案,還有科技檔案、專門檔案等檔案。在檔案概念差異如此大的情況下,把國外適用檔案館的有關理論用于論述我國檔案管理的問題,難免出現偏差。
面對這一情況的對策有兩條,一是改革我國法定檔案的概念,縮小檔案的范圍;二是改進我們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究竟什么樣的文件可以稱為檔案在理論上可以進一步探討,但關于法定檔案概念的更改,涉及到檔案法律的修正。從我國國情出發,可行的對策是改進檔案學的理論研究。其途徑一是分類研究,例如當我們研究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時應明確,是研究檔案館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還是研究檔案室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是研究文書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還是研究科技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二是宏觀把握,在把握檔案整體概念的基礎上探討其共同的形成與運動規律。事實上我國已有這一良好傳統,例如曾三同志關于我國檔案形成規律的論述就具有相當的普遍實用性。遺憾的是在引進國外檔案學理論時有些同志忽視了中國的檔案實際,淡化了我國的檔案學理論。
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中在研究視角與方法上存在的以偏概全的問題,盡管帶有一定普遍性,但對此必須正視。我們應當轉變觀念,發揚我國檔案學研究的良好傳統,培養宏觀思考的思維方式,研究適合中國檔案實際的檔案學理論。
二、檔案學研究應以檔案館研究為主體
我國檔案學理論與實踐和國外相比,其顯著的特色是建立了基層檔案機構檔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然而基層檔案室只是檔案事業的基礎,檔案館才是檔案事業的主體,因而檔案館理論應為檔案學理論的主體。我國檔案學研究的不足之處恰恰是檔案館理論研究較為薄弱。
以檔案館理論為檔案學理論的主體具有合理性。從國外情況看,國外檔案工作實踐多是指檔案館管理實踐,目前檔案學已有的重要的基礎理論實質上都是檔案館理論或站在檔案館角度進行研究而取得的。例如前面提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全宗理論、文件價值理論,甚至構成檔案學基石的來源原則也是如此。國外檔案界之所以能取得這一共識,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與借鑒。20世紀90年代國際檔案理事會組織出版了檔案學理論專著《現代檔案與文件必讀》,馮子直在該書的序言中對其評價為:“匯集了近30年來國際檔案界學術研究的優秀成果,在國際檔案界有比較重要的影響,被公認為標志著現代檔案學研究的國際水平”。查閱該書的內容可知,無論是論述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基本法律問題,還是論述檔案的鑒定與整理,直至檔案的保護與利用,無一不是針對檔案館檔案管理實踐的。
在我國按《檔案法》規定,基層檔案室檔案管理也列入了國家檔案工作的范疇,但從法定檔案的范圍看,其主體仍是國家各級各類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基層單位保存的對國家與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有相當一部分屬進館范圍,其中的大多數最終會進入檔案館。由檔案館的宗旨所決定,對一個地區和國家而言,真正具有國家與社會意義的檔案、具有民族文化遺產性的檔案,其主體多是檔案館館藏的檔案。2002年我國公布的48組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中,有42組來自檔案館館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出于對國家檔案事業的主體是檔案館的認識,檔案學理論的主體無疑應是檔案館理論。
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檔案界長期以來卻把研究的精力過多地投入到基層檔案室工作與檔案學中所謂“熱點”問題的討論,對檔案館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相對不足。近年來雖然有關檔案館的論著有所增加,但力度仍顯不足。我國檔案界之所以在檔案理論研究上出現這一狀況是有深刻的背景的,其一,我國的檔案工作是從基層建檔工作起步的,從20世紀50年代初建立機關文書檔案工作到1959年建立科技檔案,無一不是從基層單位抓起。其二,數次社會變革中基層檔案室都首當其沖,從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到1995年開始的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無不使基層檔案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沖擊之后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都面臨著基層檔案工作的恢復與重構,其間占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其三,我國檔案學理論自身不成熟,易受外界干擾。其四,檔案館的封閉性造成自身研究的滯后。我國1980年提出開放歷史檔案,1988年頒布的《檔案法》才提出并組織檔案開放。如果以1980年作為我國檔案館開放的標志,也僅有20多年的歷史,若以1988年為標志也就十多年的歷史。由于檔案館的封閉性使其主體地位在社會上沒有被廣泛認可,極大地限制了檔案館理論的研究與發展。試想處于封閉狀態的檔案館,形同歷史文件的倉庫,還有什么理論值得研究呢。前一時期我國檔案界曾反思一個問題:中國檔案事業規模世界最大,但中國的檔案學理淪為什么沒有走向世界?當時不少學者列舉了眾多原因,例如宣傳問題、翻譯問題等等,但筆者認為盡管可能有上述原因所致,但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滯后與薄弱。如果我們的檔案館理論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深刻性、先進性,它如何能走向世界呢?當然我們也可以反省一下我國又有哪些檔案館理論能夠走向世界并為國外檔案界所借鑒。當國外的共識為檔案館理論為檔案學理論的主體的情況下,我國基層檔案工作理論再發達對他們也是缺乏針對性的。
改進我們研究的視角,把研究的重點轉向檔案館理論,不是刻意為滿足我國檔案學理論走向世界的需要,而是為發展我國檔案事業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從整體上講目前我國的檔案學理論研究還較為薄弱,例如在檔案館基本屬性、檔案館功能與職能、檔案館工作基本原則、檔案館資源建設、檔案館檔案開放與鑒定、檔案館檔案利用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入,直到目前人們都還沒有一個系統的共識。這些問題都是檔案館理論中的重大問題,也是為進一步發展檔案事業所不可回避的問題。
這里強調把研究視角轉向檔案館,并非是要拋棄基層檔案室檔案管理研究。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企業已成了市場自由競爭的主體,企業檔案工作正成為企業的自律行為;機關檔案工作經多年實踐已走上正軌。在社會變動中各項工作正逐步各就各位,檔案學研究的重心轉向檔案館的實際已經趨于成熟,為此我國應當把研究的視角與重點轉向檔案館。
三、檔案學理論研究不應過多地帶有主觀色彩
任何一部檔案學論著都是作者經過一番艱苦研究探討而成的,無不凝聚著作者的心血,但這并不能成為拒絕理論批評的理由。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的一些論著中主觀色彩的傾向是較為明顯的。毋庸置疑,檔案學理論研究應以檔案為研究對象,研究者要有自己鮮明而獨特的觀點,但在研究視角與方法上還應以社會為背景,以相關領域研究為借鑒,以有關法律法規為依據,不能僅局限于檔案的小天地,不能閉門研究,不應過多地帶有主觀色彩。
以對屬于基礎理論研究的檔案的屬性為例,在講到企業檔案的作用時,有研究者把其作用拔得太高,認為企業檔案是生產力,或認為是企業資產。在論述檔案與知識產權關系時有研究者認為:檔案的知識屬性“對人類知識的繼承與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檔案及其信息作為信息形式的一種享有信息權;信息產權屬知識產權的范疇,它受到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保護”。“檔案及其信息屬于知識產權的范疇”,“檔案及其信息資源屬于《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在論述檔案館管理時,有研究者認為檔案館工作是知識管理的一部分。這些論述的主觀愿望是好的,總希望檔案的作用更大些,但這種主觀色彩較濃的論述,很難得到企業和社會的認同。在講到檔案的屬性與作用時,筆者以為不能局限于檔案的小圈子里閉門研究、自我拔高,要站在社會角度、站在相關法規角度來看檔案,要弄清這些基本術語在相關領域的含義及有關法規的解釋。事實上這么多年過去了,客觀現狀是哪一個光環也沒有降到檔案頭上,檔案依然是檔案。提高檔案的社會地位,要靠體現檔案的價值來實現,不是靠人為的理論拔高來實現的。例如企業檔案與生產力的關系,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但時間過去20年的今天,有多少理論成分被實踐所接受呢?再以知識管理為例,知識管理是以知識為主要資源,以知識的獲取、處理、共享、利用與創新為基本內容,以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為根本目標的管理模式,而綜合檔案館的檔案管理怎么能算是知識管理呢?在認識檔案與檔案館的社會作用時,我們不妨看看國外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情況,歐美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它們的檔案學研究中,例如在《現代檔案與文件管理必讀》中出現較多的是文化遺產、國家記憶、文化功能、歷史證據、研究職能等詞,似乎找不到資產、生產力、知識管理等用語,筆者以為這樣的定位還是客觀的。
以檔案信息化管理為例,目前檔案界急于求成的心理較顯著,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課題立項都往信息化上擠,檔案信息化似乎成了檔案工作中的當務之急。但什么是檔案信息化呢?我們不妨看一下馮子直2002年的一段講話:“什么是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這是一個探討多年的問題。關鍵是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有哪些項目以及定量的標準、指標。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是什么樣子、達到什么標準、指標就算是實現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了,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有沒有一個檔案現代化、信息化的指標體系?如果還沒有,那我就建議國家檔案局和中國檔案學會專門搞一個課題組,調查了解國際檔案理事會或美、加、澳、法、英、德等國家有無這方面的指標體系,或者專門研究它們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網絡化是怎樣進行的,有些什么項目、指標、達到了什么程度,對此進行專題研究”。如果這一說法成立,可以說目前相當一部分對檔案信息化研究的論著主觀色彩明顯,對于我國檔案信息化管理的研究多少帶有一些盲目性,而缺乏針對性和務實性。
回顧近20年來的檔案學理論研究,當我們翻閱檔案學的專著和期刊時可以檢閱一下哪些論著能夠經受時間的考驗。筆者感到,能經受住時間考驗的是那些務實探索檔案學基本理論與實踐的論著,是那些視角寬廣、思想深刻、實事求是的論著,凡是脫離中國檔案事業實際、盲目引用其他學科和國外檔案學理論的論著都是難以持久的。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從回顧歷史中找到改進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的理由與方向。
參考文獻:
1.侯俊芳:《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對檔案及其信息資源的保護》,《檔案學通訊》2003年第3期。
2.馮子直:《積極實現由傳統檔案工作向信息化檔案工作的轉變》,《檔案學研究》2002年第3期。
3.彼得?瓦爾蚋主編:《現代檔案與文件管理必讀》,檔案出版杜1992年版。
(郭紅解、黃曉瑾摘自《檔案學》2005?3 原載《檔案學通訊》2005?1)
一、檔案學理論研究應從我國檔案實際出發
檔案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是要解決研究對象的問題。顧名思義,檔案學理論研究不管是研究檔案(文件)的運動規律,還是研究檔案的價值,都要以檔案為對象,而我國的檔案學理論研究則應以我國關于檔案的概念為出發點。這一問題看似理所當然,但要做到準確運用概念卻不那么容易。其原因之一是我國檔案概念的外延較大。以法定檔案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檔案法》)指出:“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這種歷史紀錄,不論存放地點均視為檔案,它可以存放在檔案館或檔案室里,甚至也可以存放在家庭和個人手中;也不論保管時限均視為檔案,它可以是永久保管或長達50年長期保管的,甚至也可以是只保管15年以下(當然也包括只保管3-5年)短期保管的。檔案概念外延如此之大,使我們在研究中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對象時往往難以把握。其原因之二是受研究者視角的局限。我國檔案工作者的職業特點是分工細但缺乏綜合,例如,在機關、企事業單位中從事檔案管理的同志不一定熟悉檔案館的具體業務與要求,在學校講授文書檔案管理學課程的同志不一定對科技檔案管理學有很系統深入的研究。由于對檔案工作業務(包括檔案館與檔案室的)與檔案學學科內容缺乏整體的把握,致使在理論研究中缺乏宏觀思考,往往局限于個人從事本單位的管理對象和教學內容的視野。由上述原因所致,使以往的檔案學理論研究往往帶有片面性,其研究成果雖冠以“檔案”名義,但實則與我國的檔案概念多少存在著差距。例如在關于文件運動規律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認為:文件運動規律的三大理論是檔案學理論中最基本的理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文件運動的線性特征,全宗理論是文件運動的群體特征,文件價值理論是文件運動的動力特征。應該說研究者的這種探討精神是可貴的,研究也是有成果的,能站在一個較高層面上進行綜合思考。然而,如果站在檔案整體的高度來看,不免令人產生疑惑,它是否為建立在我國檔案概念基礎上的檔案(文件)運動的普遍規律,例如它對檔案館以外的檔案是否適用?筆者以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全宗理論、文件價值理論所體現的運動特征對檔案館的檔案是適用的,但對我國廣大企事業單位與機關檔案室(尤其是沒有進館任務者)的檔案是不完全適用或不適用的,因為這些單位檔案文件的運動既不是按全宗特征來運動的,也不是都遵循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運動的。這些單位文件的每次歸檔(運動)只是全宗構成的一部分,而且運動階段也僅到檔案室,暫存和永久保存場所是合而為一的。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全宗理論、文件價值理論這些在國外形成的檔案學經典理論為什么用以說明中國的檔案文件運動規律顯得針對性不很強呢?答案只有一個,由于各國關于檔案概念的不同所致。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最早出現在美國,當時為了解決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累的大量文件致使保管費用過高的問題,需要組建文件中心或中間檔案館暫存。在美國是把經挑選進館研究保存的文件才稱為檔案的,因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對類似美國定義檔案概念的國家是適用的。再如全宗理論,它主要是檔案館的整理理論,其產生背景是當時為糾正法國國家檔案館單純按事由原則整理封建政權遺留檔案帶來的混亂,并不是針對基層單位檔案整理的。而在我國關于檔案的概念與外國不相同,檔案的范疇不僅包括檔案館的檔案,也包括基層檔案機構的檔案;不僅有文書檔案,還有科技檔案、專門檔案等檔案。在檔案概念差異如此大的情況下,把國外適用檔案館的有關理論用于論述我國檔案管理的問題,難免出現偏差。
面對這一情況的對策有兩條,一是改革我國法定檔案的概念,縮小檔案的范圍;二是改進我們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究竟什么樣的文件可以稱為檔案在理論上可以進一步探討,但關于法定檔案概念的更改,涉及到檔案法律的修正。從我國國情出發,可行的對策是改進檔案學的理論研究。其途徑一是分類研究,例如當我們研究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時應明確,是研究檔案館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還是研究檔案室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是研究文書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還是研究科技檔案的形成與運動規律。二是宏觀把握,在把握檔案整體概念的基礎上探討其共同的形成與運動規律。事實上我國已有這一良好傳統,例如曾三同志關于我國檔案形成規律的論述就具有相當的普遍實用性。遺憾的是在引進國外檔案學理論時有些同志忽視了中國的檔案實際,淡化了我國的檔案學理論。
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中在研究視角與方法上存在的以偏概全的問題,盡管帶有一定普遍性,但對此必須正視。我們應當轉變觀念,發揚我國檔案學研究的良好傳統,培養宏觀思考的思維方式,研究適合中國檔案實際的檔案學理論。
二、檔案學研究應以檔案館研究為主體
我國檔案學理論與實踐和國外相比,其顯著的特色是建立了基層檔案機構檔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然而基層檔案室只是檔案事業的基礎,檔案館才是檔案事業的主體,因而檔案館理論應為檔案學理論的主體。我國檔案學研究的不足之處恰恰是檔案館理論研究較為薄弱。
以檔案館理論為檔案學理論的主體具有合理性。從國外情況看,國外檔案工作實踐多是指檔案館管理實踐,目前檔案學已有的重要的基礎理論實質上都是檔案館理論或站在檔案館角度進行研究而取得的。例如前面提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全宗理論、文件價值理論,甚至構成檔案學基石的來源原則也是如此。國外檔案界之所以能取得這一共識,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與借鑒。20世紀90年代國際檔案理事會組織出版了檔案學理論專著《現代檔案與文件必讀》,馮子直在該書的序言中對其評價為:“匯集了近30年來國際檔案界學術研究的優秀成果,在國際檔案界有比較重要的影響,被公認為標志著現代檔案學研究的國際水平”。查閱該書的內容可知,無論是論述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基本法律問題,還是論述檔案的鑒定與整理,直至檔案的保護與利用,無一不是針對檔案館檔案管理實踐的。
在我國按《檔案法》規定,基層檔案室檔案管理也列入了國家檔案工作的范疇,但從法定檔案的范圍看,其主體仍是國家各級各類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基層單位保存的對國家與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有相當一部分屬進館范圍,其中的大多數最終會進入檔案館。由檔案館的宗旨所決定,對一個地區和國家而言,真正具有國家與社會意義的檔案、具有民族文化遺產性的檔案,其主體多是檔案館館藏的檔案。2002年我國公布的48組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中,有42組來自檔案館館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出于對國家檔案事業的主體是檔案館的認識,檔案學理論的主體無疑應是檔案館理論。
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檔案界長期以來卻把研究的精力過多地投入到基層檔案室工作與檔案學中所謂“熱點”問題的討論,對檔案館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相對不足。近年來雖然有關檔案館的論著有所增加,但力度仍顯不足。我國檔案界之所以在檔案理論研究上出現這一狀況是有深刻的背景的,其一,我國的檔案工作是從基層建檔工作起步的,從20世紀50年代初建立機關文書檔案工作到1959年建立科技檔案,無一不是從基層單位抓起。其二,數次社會變革中基層檔案室都首當其沖,從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到1995年開始的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無不使基層檔案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沖擊之后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都面臨著基層檔案工作的恢復與重構,其間占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其三,我國檔案學理論自身不成熟,易受外界干擾。其四,檔案館的封閉性造成自身研究的滯后。我國1980年提出開放歷史檔案,1988年頒布的《檔案法》才提出并組織檔案開放。如果以1980年作為我國檔案館開放的標志,也僅有20多年的歷史,若以1988年為標志也就十多年的歷史。由于檔案館的封閉性使其主體地位在社會上沒有被廣泛認可,極大地限制了檔案館理論的研究與發展。試想處于封閉狀態的檔案館,形同歷史文件的倉庫,還有什么理論值得研究呢。前一時期我國檔案界曾反思一個問題:中國檔案事業規模世界最大,但中國的檔案學理淪為什么沒有走向世界?當時不少學者列舉了眾多原因,例如宣傳問題、翻譯問題等等,但筆者認為盡管可能有上述原因所致,但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滯后與薄弱。如果我們的檔案館理論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深刻性、先進性,它如何能走向世界呢?當然我們也可以反省一下我國又有哪些檔案館理論能夠走向世界并為國外檔案界所借鑒。當國外的共識為檔案館理論為檔案學理論的主體的情況下,我國基層檔案工作理論再發達對他們也是缺乏針對性的。
改進我們研究的視角,把研究的重點轉向檔案館理論,不是刻意為滿足我國檔案學理論走向世界的需要,而是為發展我國檔案事業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從整體上講目前我國的檔案學理論研究還較為薄弱,例如在檔案館基本屬性、檔案館功能與職能、檔案館工作基本原則、檔案館資源建設、檔案館檔案開放與鑒定、檔案館檔案利用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入,直到目前人們都還沒有一個系統的共識。這些問題都是檔案館理論中的重大問題,也是為進一步發展檔案事業所不可回避的問題。
這里強調把研究視角轉向檔案館,并非是要拋棄基層檔案室檔案管理研究。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企業已成了市場自由競爭的主體,企業檔案工作正成為企業的自律行為;機關檔案工作經多年實踐已走上正軌。在社會變動中各項工作正逐步各就各位,檔案學研究的重心轉向檔案館的實際已經趨于成熟,為此我國應當把研究的視角與重點轉向檔案館。
三、檔案學理論研究不應過多地帶有主觀色彩
任何一部檔案學論著都是作者經過一番艱苦研究探討而成的,無不凝聚著作者的心血,但這并不能成為拒絕理論批評的理由。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的一些論著中主觀色彩的傾向是較為明顯的。毋庸置疑,檔案學理論研究應以檔案為研究對象,研究者要有自己鮮明而獨特的觀點,但在研究視角與方法上還應以社會為背景,以相關領域研究為借鑒,以有關法律法規為依據,不能僅局限于檔案的小天地,不能閉門研究,不應過多地帶有主觀色彩。
以對屬于基礎理論研究的檔案的屬性為例,在講到企業檔案的作用時,有研究者把其作用拔得太高,認為企業檔案是生產力,或認為是企業資產。在論述檔案與知識產權關系時有研究者認為:檔案的知識屬性“對人類知識的繼承與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檔案及其信息作為信息形式的一種享有信息權;信息產權屬知識產權的范疇,它受到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保護”。“檔案及其信息屬于知識產權的范疇”,“檔案及其信息資源屬于《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在論述檔案館管理時,有研究者認為檔案館工作是知識管理的一部分。這些論述的主觀愿望是好的,總希望檔案的作用更大些,但這種主觀色彩較濃的論述,很難得到企業和社會的認同。在講到檔案的屬性與作用時,筆者以為不能局限于檔案的小圈子里閉門研究、自我拔高,要站在社會角度、站在相關法規角度來看檔案,要弄清這些基本術語在相關領域的含義及有關法規的解釋。事實上這么多年過去了,客觀現狀是哪一個光環也沒有降到檔案頭上,檔案依然是檔案。提高檔案的社會地位,要靠體現檔案的價值來實現,不是靠人為的理論拔高來實現的。例如企業檔案與生產力的關系,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但時間過去20年的今天,有多少理論成分被實踐所接受呢?再以知識管理為例,知識管理是以知識為主要資源,以知識的獲取、處理、共享、利用與創新為基本內容,以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為根本目標的管理模式,而綜合檔案館的檔案管理怎么能算是知識管理呢?在認識檔案與檔案館的社會作用時,我們不妨看看國外檔案學理論研究的情況,歐美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它們的檔案學研究中,例如在《現代檔案與文件管理必讀》中出現較多的是文化遺產、國家記憶、文化功能、歷史證據、研究職能等詞,似乎找不到資產、生產力、知識管理等用語,筆者以為這樣的定位還是客觀的。
以檔案信息化管理為例,目前檔案界急于求成的心理較顯著,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課題立項都往信息化上擠,檔案信息化似乎成了檔案工作中的當務之急。但什么是檔案信息化呢?我們不妨看一下馮子直2002年的一段講話:“什么是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這是一個探討多年的問題。關鍵是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有哪些項目以及定量的標準、指標。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是什么樣子、達到什么標準、指標就算是實現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了,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有沒有一個檔案現代化、信息化的指標體系?如果還沒有,那我就建議國家檔案局和中國檔案學會專門搞一個課題組,調查了解國際檔案理事會或美、加、澳、法、英、德等國家有無這方面的指標體系,或者專門研究它們檔案工作現代化、信息化、網絡化是怎樣進行的,有些什么項目、指標、達到了什么程度,對此進行專題研究”。如果這一說法成立,可以說目前相當一部分對檔案信息化研究的論著主觀色彩明顯,對于我國檔案信息化管理的研究多少帶有一些盲目性,而缺乏針對性和務實性。
回顧近20年來的檔案學理論研究,當我們翻閱檔案學的專著和期刊時可以檢閱一下哪些論著能夠經受時間的考驗。筆者感到,能經受住時間考驗的是那些務實探索檔案學基本理論與實踐的論著,是那些視角寬廣、思想深刻、實事求是的論著,凡是脫離中國檔案事業實際、盲目引用其他學科和國外檔案學理論的論著都是難以持久的。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從回顧歷史中找到改進我國檔案學理論研究的理由與方向。
參考文獻:
1.侯俊芳:《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對檔案及其信息資源的保護》,《檔案學通訊》2003年第3期。
2.馮子直:《積極實現由傳統檔案工作向信息化檔案工作的轉變》,《檔案學研究》2002年第3期。
3.彼得?瓦爾蚋主編:《現代檔案與文件管理必讀》,檔案出版杜1992年版。
(郭紅解、黃曉瑾摘自《檔案學》2005?3 原載《檔案學通訊》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