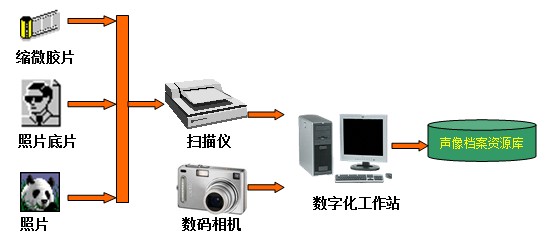檔案的起源
一、檔案起源諸說關于檔案的起源及其歷史背景歷來眾說紛紜。要搞清這個問題,不僅需要借助考古學、文字學、歷史文獻學、社會發展史、民俗學等相關學科中相關課題的研究進展,對有關歷史資料進行充分的查證、分析和研究,而且取決于對檔案本質屬性的正確認識。1947年,四川大學教授毛坤在為黃彝仲所著《檔案管理之理論與實際》一書所作的序中寫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老子為柱下史,今日胥謂圖書館之濫觴,實則所掌皆檔案也。”同年,許同莘的《公牘學史》認為“唐虞以前已有檔案”。20世紀50年代,我國檔案界曾有“檔案是否是階級社會產物”的論爭,此后又有進一步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外一些檔案學者認為檔案產生于國家形成之后,但至今國內外對此仍有多種觀點并存。
中外學者關于檔案起源的觀點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文字是產生檔案的必要條件。自從人類發明了文字,就開始用文字記錄社會活動,并將這些記錄保存下來,成為檔案。第二種觀點認為文字和國家的出現是檔案產生不可缺少的條件。隨著階級的出現和國家的形成,為了管理大規模的生產,進行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或戰爭,國家需要有文字記錄作為管理國家和交際的工具,于是產生了文書,保存起來便形成了檔案。第三種觀點認為以原始記事方法形成的記錄就是檔案,如結繩、刻契、編貝、結珠、圖畫等。這些研究,對于探索檔案的起源,從而了解檔案的性質,都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意義。
歷史事實表明,檔案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文明產物,檔案是人們社會實踐活動的歷史記錄。人類在原始群和原始公社前期的漫長年代里,沒有也不可能創造記錄和表達語言的書寫符號,作為擴大語言交際功能的文化工具。遠古人只能靠語言和動作表達思想,憑人腦記憶存儲信息。但是,聲音的傳達受到時間和空間的極大限制,不能直接通達遠處,無法準確地存儲起來備用,更難以流傳于后人。人腦記憶和口傳,也是難免遺忘和失真的。為了彌補這些缺陷,人們創造了圖畫、“結繩記事,’和“刻木為契”等記事方法。圖畫或巖畫是古代人類最早采用的一種記錄事實和表達思想的方法,發展水平較高的圖畫已有一些“語言符號”的作用,它曾在許多部落和部族中廣泛使用。現在五大洲有100多個國家都發現了巖畫,例如,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穴巖畫和法國封德·高姆洞穴巖畫,反映了舊石器時代各種野獸的形象和日常狩獵活動。在阿塞拜疆的加布斯坦P21發現了6 000多幅巖畫,上面刻有獵牛的場面等(圖2一1)。結繩記事是古代流行很廣的一種記事方法,唐朝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引《九家易》寫道;古者無文字其有約事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古代秘魯、埃及、日本等國家,我國的高山族、哈尼族、獨龍族等少數民族都有過結繩之事。①參見王鳳陽:《漢字學》,47~48頁,長春.吉林文史出版杜,1989 刻契就是在竹、木、骨等材料上刻上各種痕跡和記號,以記事、記數或傳達信息、我國很多地區古時都有刻契記事的做法一些少數民族.如獨龍族、怒族、基諾族瑤族等直至解放前夕還保留有刻契記事的方法。所謂“編貝”、結珠’,就是把各色的貝殼磨成扁圓形的小珠,或者直接把穿孔的貝殼按各種習慣的方式穿在繩子或樹皮之類的纖維上,編成各式的花紋記載不同的事情。我國臺灣土人曾使用過編貝或結珠記事,美洲的若于印第安人部落也用過這種方法稱為“萬普穆”。
圖畫、結繩、刻契等原始記事方法與一定思想聯系了起來在一定范圍內有約定俗成的涵義,可以保存,可以傳遞起著記錄和備忘、憑證及信守的作用。但它們畢竟都是標記和符號,沒有記錄語言和有聲語言不相聯系,因此具有記事人的隨意性,其意義是不確定的。這些記事方法R能幫助人們喚起某些具體事物的記憶不能表達確切、完整、拙象的思想和語義需要輔以一定的口頭說明才能明確其涵義、因此,圖畫、結繩、刻契等原始記事材料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檔案,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把依靠此類原始記事方法記憶的時代稱為“助記憶時代’。
社會生產的發展人際交往的擴大人類智力的提高,文字的發明恃別是作為記錄語言的文字——表音字的出現。為準確地記錄事實提供了條件,為檔案的產生提供了客觀可能性、在人類歷史的復雜過程中,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文字的產生和應甲情況不盡相同。從世界歷史發展過程看特別是從一些文明古老的國家和地區的旱期歷史來考察,文字一般產生和應用干原始公社制度解體的時期,即國家形成之前的原始社會后期。
二、中國檔案起源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中國古代文字的產生和應用,不僅標志著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的發展水平,而且為產生文字記錄的檔案提供了重要的條件。關于中國文字起源最為流行的傳說,是黃帝時期倉頡始造文字。文字是人類在長期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出于記事和傳遞信息的需要,在人類群體創造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和完善的,不可能主要是某個人的獨創。《茍子·解蔽》認為:“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可能是古代特別是黃帝族整理文字和保存文書的代表人物的象征。
在古文獻中關于保存和傳留書契典籍的記載不絕于史。《尚書正義》稱:“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幾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日尚書。”現在一般也認為,《尚書》是上古歷代文書的匯編,后世保存下來的只有《堯典》至《秦誓》29篇,其中有些是后人補充進去的。《尚書》保存了有關虞、夏特別是商周的重要史料,它是迄今我國最古的歷史文件匯編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文集。古代傳說的各種記載,其人其事未必完全準確。但總的看來,還是大致反映了從黃帝到堯、舜時代前后,“炎黃子孫”發明文字并應用于記錄和保存文書、檔案的某些情景。現在我們將這些傳說與考古發掘的實物聯系起來考察,則更能顯示出這些記載的文獻價值。
仰韶文化是中國先民創造的重要文化之一,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其中西安半坡村出土的距今6 000年左右的陶器上,有二三十種刻畫符號。郭沫若的《中國史稿》和《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認為:“這些刻記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在陜西臨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遺址中,也曾多次發現刻在陶器上的符號。僅姜寨就發現i00多個、40多種符號,有的與半坡的符號相同。上述遺址分布的范圍達3萬平方公里之廣。以上材料說明,仰韶文化遺址的刻畫符號,是原始先民在比較廣泛的地區里和較長的時期內比較普遍使用的、帶有某些規范性的記事符號。對這些記事符號,雖然至今尚未更多識讀,但是可以看出,中國原始文字記錄的產生時間可能距今已有5000多年。也可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檔案大致的起源時期。文字的產生、文字記錄的應用、檔案的產生,中間不可能有很長的空白,有了文字就會使用,使用的記錄保存下來,就其性質來說就是古代的檔案。
屬于龍山文化時代晚期的文字至今已有發現。陜西省考古工作者于20世紀80年代在西安市西郊斗門鄉花園村發掘了一個原始社會遺址,內有一批原始先民刻寫的甲骨文,文字被分別刻寫在骨笄、獸牙和獸骨上,現已清理出一批單體P23字、這批甲骨文字體與殷代甲骨又字體接近、有關專家分析認為,這里出土的甲骨文是距今大約4500年到5000的文字。對已出土的各種文化遺跡進行綜合分析,在這時期出現文字和保存文宇記錄也是比較可信的、山東大汶口文化中發現的刻在陶尊上的文宇符號,出現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關專家認為,陶尊文字是我國文字的遠祖,屬于意符文學,大汶口文化已經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時代了。①參見唐蘭:《從大汶口文比的陶尊文字看我國最甲文化的年代》,載《光明日報》1997—07—14。
國家形成之后,為了適應繼續發展的杜會生產利更為廣泛的社會生活,特別是進行國家的管理,需要比較有條理、系統的文書來記錄和傳遞各種信息。這些文書記錄又被比較系統地保存起來形成了數量可觀的古代王朝檔案。1899年在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墟發現的甲骨文就是商王朝使用的一種文書,屬于約公元前l300一前1100年的遺物。此后歷經多次發掘、共得15萬余片甲骨。商代甲骨文,是迄今我國大量發現的最早的較為系統的文字和古代檔案。因這些文字刻寫在龜甲和獸骨上,所以被稱做甲骨文,又因甲骨文多是王室占卜的記錄,以及與占卜有關的記事文宇,所以又叫“卜辭’。
多年來,經過深入研究,據現今不完全統計,甲骨文的字數約有4500個,說明商代晚期的文宇已相當發達。從其文字結構分析后人所謂的“六書”或稱為“六義’,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這六種構成文字的原則。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備,已經形成比較嚴密的文字系統,顯然, 這樣較為完善的文字,是經過長期發展形成的,因而殷商時期的甲骨文書應當不是歷史上最初始的文書和檔案。據郭沫若的研究,他認為中國文字的發展,到商代后期已經基本成熟,殷商的甲古文字毫無疑問是經過了至少兩三千年的發展的、所以說,由于中國原姑社會后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們之間社會交往的擴大社會管理和 生產管理的加強,以及人們智力的提高,在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時期產生文字記錄和保存早期檔案,也是合乎歷史邏輯的。
三.外國檔案起源
古代埃及是世界文明的搖籃之一,在公元前 5000多年,即早期王國以前就發明了文字、有材料表明古埃及在第一王朝以前,史官們便用墨水把文字寫到儲物罐上了,而目這些文字的筆跡已有比較流利和穩健的特色。到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時期(約公元前3000 前2700年)用墨水寫在器皿上的象形文字筆畫越來越流利了。出自公元前2000多年的埃及紀年石刻,碑文上載有前王朝至古王國第五王朝(公元前4000一前2420年)各法老的名字(他們進行遠征等活P24動),以及尼羅河水位的標記。這部分石刻斷片現藏于意大利西西里的巴勒摩博物館,因而被稱為“巴勒摩石碑”。它是現存的埃及最古老的年代紀,成為研究埃及早期歷史的重要史料。
世界古代文明的另一個搖籃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希臘文為“美索不達米亞”,意即兩河之間的地方。兩河流域有亞述、巴比倫、阿卡德和蘇美爾等文明。最古老的奴隸制國家產生在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大約公元前3000一前2500年,蘇美爾地區開始了最初國家的形成過程。考古學和世界史的材料表明,兩河流域最古的文獻(約公元前4000年),就是關于供奉祀神費用的農場的文件。蘇美爾人在烏魯克后期(約公元前3200年)產生了最古老的圖形文字,是后來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前身。最初是圖形符號,后來發展為表音符號和指意符號,二者一起組成詞組。這種文字用蘆管刻畫在泥板上曬干后成為可以長久保存的文書,文字筆畫如楔形,因此稱為楔形文字(因其形似箭頭,又稱箭頭文字)。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古代埃及、腓尼基、印度、中國等使用象形文字;古代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巴比倫、亞述、波斯等使用楔形文字。這些古老文字是人類積累經驗、擴大智慧、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工具,顯然也是產生檔案必不可少的條件。
最早的古代檔案是通過考古發掘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古是人們窺視古代檔案和檔案工作的窗口。17世紀,從古波斯(今伊朗境內)王宮廢墟中發掘的刻寫在泥板上的文字記錄,引起了一位意大利商人的好奇。他復制了一份拓片帶回歐洲,引起了歐洲一些史學家的興趣。1799年入侵埃及的法國軍隊在羅塞達城挖戰壕時,發現了一塊石碑,上面刻有三種文字:上部為古埃及僧侶體象形文字,中間是古埃及世俗體象形文字,下部是希臘文。1822年由法國青年埃及學家商博良解譯成功,使世人了解到它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為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立的頌德碑。這塊石碑引起了學者們的更大興趣,按發掘地點被命名為羅塞達石碑(圖2—2),現存于英國倫敦博物館。羅塞達石碑的發現和解譯成功,促進了考古學的發展,19世紀成了考古的盛行時期。英、法、德、荷、意等許多歐洲國家及美國都派遣了考古隊或探險隊到古代東方各國進行考古發掘。他們不僅發現了大量文字遺物,還發現了不少古代檔案庫。
在埃及發現最多的是石刻檔案(又稱題銘檔案)、紙草檔案和泥板檔案。如1885年在開羅以南287公里處發現的埃爾一阿馬爾奈檔案庫遺址,曾是一座法老檔案庫,考古工作者從中清理出許多楔形文字泥板檔案。
在兩河流域發現最多的是泥板檔案。從1846年起,英、法等國考古隊陸續在古亞述首都尼尼微進行考古,發掘出公元前lo世紀一前6世紀的泥板檔案兩萬余塊。1875年,在古羅馬帝國龐培城的遺址(在今意大利那不勒斯東南方)發掘出一箱蠟板檔案,共127塊。1900年以來,英國、意大利等國的考古人員在希臘克里特島克諾索斯古城遺址發現了米諾斯王宮檔案庫,從中清理出4 000多塊泥板檔案,分門別類保存在木箱和石膏箱子里。1939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希臘皮羅斯城遺址發現了一個完整的檔案庫,從中獲得楔形文字的泥板檔案618塊。
總之,自18世紀末以來的考古發掘,不僅促進了考古學的發展,而且為史學研究挖掘出大量用文字書寫的古代檔案。它們記載了人類第一個階級社會——奴隸社會的發展歷史,從而證明了古代埃及、古代兩河流域等古代東方奴隸制國家是人類文明的最早發祥地,也是最早產生檔案和檔案工作的地方。
從中外檔案起源的過程可以看出,檔案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它以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類交往的擴大以及文字發明為基礎,產生于原始公社向奴隸制過渡的時期。由石器時代進入金屬時代以后,生產力空前提高,階級和國家的雛形逐漸產生,強化社會關系和社會管理的實踐要求使用文書以記錄和傳遞信息,而文字的出現又為文書記錄提供了工具。同時,各種社會實踐活動的繼續和發展,需要人們存儲有價值的文字信息,以資查考和充作憑證,因此而保存起來的文書則成為檔案。隨著國家的出現和社會的繼續發展;逐漸形成了比較有條理的文書,進而保存積累成較有系統的檔案。因此,檔案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文字信息記錄,是社會發展中的第一代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