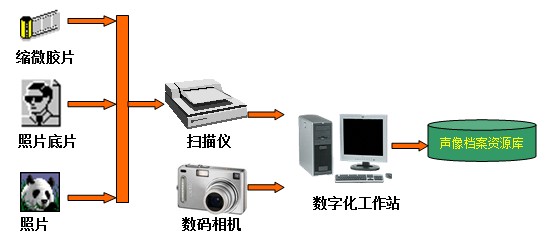“實物檔案”是90年代初檔案界一些同志提出的一個新的概念。近十年來、張家儀、李焱、范世清、陳永斌、霍振禮、向全福、謝瑞芝、肖寧生、吳軍梅等人先后撰文各抒己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遺憾的是尚未形成共識,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筆者認為,文物與檔案如何區別,實物是否可以作為檔案,既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亟待弄清的實踐問題。
一、造成檔案與文物界限不分的社會歷史根源
造成檔案與文物界限不分的社會歷史根源是多種多樣的,最主要的有如下3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人類認識規律的影響、現行法律上的自相矛盾。
1、傳統文化的影響 人類社會是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人們的社會分工也是遵循從統到分,從粗到細的規律逐步形成的。在中國社會的歷史長河中,相當長的時期里都是融文物、圖書、檔案于一體的。有報道說我國的唐宋檔案除了遼寧省檔案館有幾件唐代檔案,安徽省檔案館有點宋代檔案外,其它大都保存在博物館和圖書館,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一代沿襲一代,區分文物與檔案的意識也就十分淡薄。直到今天的實踐中,每每遇上具交叉屬性的事物時,不是按事物本質屬性去判定歸屬,而是看誰捷足先登。對這種現象李焱在《也談檔案與文物》一文中是這樣揭示的:“事實上檔案和文物的工作對象存在著交叉重復現象,同一物件有可能既是文物同時也是檔案。特別是在當今,檔案界的理論研究還遠遠不夠,對于檔案的定義還沒有一個科學的統一表述,有許多具有檔案、文物雙重身份的物件的歸屬問題也沒有一個具體明確的準則,而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如甲骨文、銘文等并不是因為檔案館和文物館進行協調工作后由于價值取向等問題而決定由文物館收藏,僅僅是由于檔案事業起步較遲、發展較緩而為文物部門先行千步所致。”
2、人類的認識規律的影響 任何理論的產生都來自于一定的實踐,沒有實踐基礎的理論是不存在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早在幾千年前便產生了文字,其悠久的歷史,注定了它有著豐富的實踐基礎。在我國,檔案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但完整意義上的檔案工作歷史并不長。在紙張未面世以前,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已經發現對某種既往活動信息存在著需要。而這種信息總是附著在龜甲、獸骨、縑帛、鐘鼎、竹木、石頭等物質之上,的他們將這些信息保管起來備以查考,形成了我國最早的檔案工作。唯物論的認識論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各項實踐的產生總是根據人類社會需要的緩急程度,按先具體后抽象的秩序決定先后的。當人們的感性認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上升為理性認識,再經過實踐的驗證,又逐步將零星的理性認識系統化,最終形成一門學問。由于早期檔案信息與載體的不可分離性,給人的錯覺是檔案就是一種物體,因而在檔案工作中往往把一些本來屬于文物范疇的東西(如產品樣品、古錢幣、鐘鼎、名人遺物等)當作檔案。按照人類的認識總是從具體到抽象的規律,人們把這些特殊物作為檔案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它們畢竟從某個側面記錄了人類某方面社會活動的信息,是對某種歷史的反映。不過這些物質只能間接地反映出某種信息,而不是對信息的直接記錄,不具有檔案的本質屬性。
3、《檔案法》和《文物保護法》概念交叉造成的矛盾。在《檔案法》中是這樣表述的:“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而《文物保護法》第二條規定“受國家保護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物包括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和壁畫,具有重要意義的建筑物、遺址、紀念物、歷史上各時代的珍貴藝術品、工藝美術品;反映各時代社會制度、生產、生活的代表性實物,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具有科學、歷史、藝術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在這兩個法律中“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具有科學、歷史、藝術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和“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概念交叉,客觀上造成人們無所適從。《檔案法》第三章第十二條規定:“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保存的文物、圖書資料同時是檔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上述單位自行管理。”《檔案法》這一規定實際上是對檔案的雙重身份作了肯定。同時也承認目前對于這部分具雙重身份的檔案的實體管理與實體歸屬問題暫無比現行做法更好的方法。可是由于檔案和文物這種在現實中的交叉重復關系,勢必將會隨著社會的發展,檔案事業和文物事業的發展,而在二者之間產生一系列的矛盾。
二、“實物檔案”概念不成立
顧名思義,實物檔案即具有檔案屬性的實物通過收集整理而轉化成的檔案。實物能否成為檔案中的一個門類呢?唯物辯證法認為,決定一事物與它事物的區別的不在于它們的外形特征,而在于它們內在的本質的特征。石頭、鐵、煤炭、水晶之所以是不同的事物,是由于它們內在的元素結構不同,而表現出的不同形態。從理論上講,實物檔案的內涵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實物,一個是檔案,客觀具體是它的外在特征,原始記錄性是它的內在特征。實物之所以不能成為檔案,關鍵在于這些實物不具有檔案的本質屬性?原始記錄性。我們知道,檔案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記錄,是人們辦理完畢保存備查的一種文件,它是融原始性與記錄性于一體的特殊事物。所謂原始性,就是說它是人們在社會實踐活動的當時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事后編纂和加工的。所謂記錄性,自檔案學誕生以來,檔案界研究的“記錄”無一例外的是指狹義的記錄,即用文字、符號和圖像等記錄工具直接將人類社會活動信息記錄在特定載體(如紙張、膠片、磁盤、光盤等)上,而人們只要掌握了識別這些文字、符號和圖像的工具就能獲取其中的信息。而實物檔案具不具備這些特征呢?不可否認,檔案館、室所收藏的實物,(包括古代用來調動軍隊的虎符,封建帝王賜予的尚方寶劍)也許具有原始性,并能傳遞給人們人類既往活動的信息,但它并不能成為檔案,理由是它不具有狹義的“記錄”性質,不是通過文字、符號和圖像等記錄手段直接將信息記錄于特定載體,反映某一行為的全過程,而是通過某事物的形態與結構反映某種行為的結果,人們只能通過對實物的觀察、分析和推測去獲得某種深層次的信息。(如法國的比薩斜塔,我們僅憑外觀只能獲得塔的結構、形狀和傾斜角度等信息,如果有檔案可查的話,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建造年代,還可以了解到塔傾斜的原因,弄清它是巧奪天工的杰作,還是地殼變遷的結果)。有人認為,實物檔案是用一種具體的、直觀的形式記錄信息。這事實上是將狹義的“記錄”廣義化了,按此觀點推論,上至天上的云彩、星星,下至地下的巖層、礦石,無不從一定角度記錄一定的信息,它們如果都可以成為檔案,那世間的萬事萬物也就都是檔案了。這樣一來,文物不就消亡了?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來分析實物能不能成為檔案。在這些年開展的關于實物檔案的討論中,不少的人認為,實物檔案是檔案的一種,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他們的理論及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關于檔案概念的界定:“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由此得出結論:檔案具有多種形式。按照檔案信息的表現形式,檔案可分為紙質檔案、聲像檔案(現代又產生了電子檔案)和實物檔案等。這些同志認為檔案部門收藏的古代的印章、刻有文字的碑匾、獎杯、獎牌、證書、錦旗、古幣、古服飾、歷史名人用物、產品樣品等都屬于實物檔案之列。其實這是對檔案概念的一個誤解。上述物體中古錢幣、古服飾、歷史名人用物無論怎么講都屬于文物,印章、碑愿、獎杯、獎牌、證書、錦旗雖可以作為檔案保存,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說它就是實物檔案,因為作為檔案部門要保存的僅僅是這些物體上記錄的某種信息而不是物本身,只不過該信息與該物體無法分離而已。假若是一塊刻有重要信息的石碑,我們不但不需要這塊石頭有多厚重,反而希望它越薄越好。由此可見,此類檔案只是載體的不同,是該與紙質檔案、電子檔案相提并論的金石檔案、縑帛檔案,而不能認為是實物檔案。
三、“實物檔案”帶來了理論與實踐的混亂
眾所周知,檔案是指辦理完畢保存備查之文件(用文字、數字、符號、圖象將信息直接記錄。到紙張、磁帶、光盤等載體的文書材料)。“實物檔案”造成的理論混亂,首先是它打破了檔案構成體系的基本要素——“文件材料,把它擴展到了自然界所有能反映一定信息的客觀物質。其次,是把狹義的采用特定記錄手段的直接“記錄”,變成了廣義的某種行為結果的間接“記錄”。其三,是忽視了信息存儲方便、傳遞快捷、復制簡單和資源共享等特點,混淆了實物反映信息與書面記錄信息的界限。其四,違背現行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明確規定“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著名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建筑物、遺址、紀念物;歷史上各時代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等屬于文物范疇,而我們硬要把具有紀念性質的獎證、獎杯和生產企業的生產樣品作為檔案。其五,導致“兩法”打架。《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把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界定為檔案,自然這些歷史記錄應該包括“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則界定“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等”屬于文物,很顯然它包括了“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的一部分。理論上的混亂,必然引起實踐上的混亂。在實踐中,檔案館室存文物,文物館室存檔案,文物搶檔案,檔案搶文物,互不相讓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尤為典型的是陳景潤的“1十2”手稿,明明是珍貴的科技檔案卻被征集到了文物部門;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契約”、東京大審判的判決書的底稿、中國“人才一號”的交流協議等,這些無論從廣義的角度還是狹義的角度理解,都屬于檔案的東西,卻偏偏保存在博物館或圖書館。
四、關于檔案與文物界定之設想
《檔案法》明確指出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在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縱觀世界百年檔案定義,無不以“文件材料”、“原始記錄”、“非現行文件”、“書寫文件、圖片、印刷品的總合”、“留待參考之文書”、“文獻記錄”等作為檔案的屬概念。可見,自古以來我們講的檔案就是指的用文字、圖表、聲像等特定手段記錄信息的特定載體。《文物保護法》明確指出: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著名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建筑物、遺址、紀念物;歷史上各時代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反映歷史上各時代、各民族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屬于文物受國家保護。對文物的解釋,《辭海》是“遺存在社會和埋藏在地下的歷史文化遺物”,《漢語大詞典》是“歷代相傳的文獻古物”。從這些定義中,我們得到什么樣的啟示呢?1.在物質形態上,檔案是各種不同形式的文件材料;文物則是有歷史、藝術、科學、史料價值,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代表性的實物(如長城、天壇、黃帝陵、黃道婆的紡車、賀龍起義的菜刀)。2.在對信息的記錄方式上,檔案是用文字、數字、圖表、聲像等記錄手段直接記錄信息,只要利用者掌握了識別這種記錄符號的本領,就能夠獲得其中的信息;文物則是用某種物質形式間接記錄信息,要了解該事物的全部信息必須借助一定的媒介(如書籍、影視等),這就是博物館、陳列室為啥要用解說詞和解說員的道理。3.從內容涉及的廣度和深度看,檔案記載著人類社會活動各個方面的信息,可以記錄下事物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具有一定深度;而文物只能記錄事物本身的結果的信息,人們只能通過物體信息去推論相關的社會信息。4.檔案信息具有方便存貯、易于傳遞等特點,而文物保管難度大,傳遞、運送不方便。由此,本人認為,檔案的落腳點應該在“文”上,即用文字、數字、圖表、聲像等記錄手段記錄著信息的紙張、磁帶、光盤等文件材料。文物的落腳點應該在“物”上,諸如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物,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代表性的今物。對于那些記錄有信息的物體,判斷它屬于檔案還是屬于文物,就是要看它的文字意義(信息價值)大于物還是物的意義大于文字意義(信息價值)。
五、如何看待檔案館、室和博物館收藏具有交叉屬性的實物
目前,我國的一些檔案館室收藏的被稱做檔案的實物,大致可以分為3種類型:一部分屬于文物(如古幣、古服飾、歷史名人用物等);一部分屬于佐證物(如獎杯、獎牌、產品樣品等);還有一部分屬于文件材料“(如證書、錦旗、牌匾等)。第一種情況顯而易見,無需贅述。為什么要把獎杯、獎牌、產品樣品作為佐證物而不作為檔案呢?因為獎杯、獎牌是通過評定或比賽而決出來的,這種評定、比賽的書面記載或聲像記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檔案,而獎杯獎牌只不過是給勝利者的一種紀念物,如果有價值的話,將來可能轉化為文物;至于產品的樣品,它只是某一設計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的佐證物,真正的檔 案應該是知識形態的產品設計文件。至于有些企業把本廠的產品也當作實物檔案加以保存,這更是不可取的。因為我們要了解某種型號的產品,完全可以通過相應的圖紙,而這些圖紙已作為科技檔案加以保存了。被“實物檔案”論者認為是實物的另一部分是證書、錦旗、牌匾,其實應該歸入文件材料之列,道理很簡單,它們的實質不在于物的意義而在于文的意義,“物”只是“文”依托的載體。證書漂亮的外殼,錦旗美麗的形式,匾牌堅硬的質地,都只是對內容的包裝,都只是文件材料的載體不同而已。由此,筆者以為,檔案館室所收藏的實物,除一部分屬于文物外,另一部分是對檔案作補充和佐證的物質,只具有檔案室保存的資料的性質,還有一部分則是待殊載體(如金屬、石料)的文件材料,也只能稱為“金石檔案”,或統稱為“其它載體檔案”,決不該稱什么“實物檔案”。
六、否定“實物檔案”的意義
綜上所述,正如有的同志認為,“實物檔案”這個概念在思維領域違背了人類對物質世界認識的規律,在檔案學理論上違背了檔案分類規則,在檔案工作的實踐中起著誤導作用。從檔案的歷史淵源上講,它不包括實物,從現代檔案工作的狀況看,它仍不該包括實物。我們否定“實物檔案”,不僅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首先,將正本清源,真正劃清檔案與非檔案的界限,建立一個準確的“檔案”概念,推進檔案學理論建設,從而更加有效的指導檔案工作的實踐。其次,便于檔案工作者把握檔案館、室工作的重點,進一步做好檔案館室的業務工作;第三,明確劃分檔案部門與文物部門的職責,理順管理關系,建立一個職、權、責關系明晰的社會分工體系,促進檔案事業與文物事業共同發展。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2004年第3期)
一、造成檔案與文物界限不分的社會歷史根源
造成檔案與文物界限不分的社會歷史根源是多種多樣的,最主要的有如下3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人類認識規律的影響、現行法律上的自相矛盾。
1、傳統文化的影響 人類社會是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人們的社會分工也是遵循從統到分,從粗到細的規律逐步形成的。在中國社會的歷史長河中,相當長的時期里都是融文物、圖書、檔案于一體的。有報道說我國的唐宋檔案除了遼寧省檔案館有幾件唐代檔案,安徽省檔案館有點宋代檔案外,其它大都保存在博物館和圖書館,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一代沿襲一代,區分文物與檔案的意識也就十分淡薄。直到今天的實踐中,每每遇上具交叉屬性的事物時,不是按事物本質屬性去判定歸屬,而是看誰捷足先登。對這種現象李焱在《也談檔案與文物》一文中是這樣揭示的:“事實上檔案和文物的工作對象存在著交叉重復現象,同一物件有可能既是文物同時也是檔案。特別是在當今,檔案界的理論研究還遠遠不夠,對于檔案的定義還沒有一個科學的統一表述,有許多具有檔案、文物雙重身份的物件的歸屬問題也沒有一個具體明確的準則,而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如甲骨文、銘文等并不是因為檔案館和文物館進行協調工作后由于價值取向等問題而決定由文物館收藏,僅僅是由于檔案事業起步較遲、發展較緩而為文物部門先行千步所致。”
2、人類的認識規律的影響 任何理論的產生都來自于一定的實踐,沒有實踐基礎的理論是不存在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早在幾千年前便產生了文字,其悠久的歷史,注定了它有著豐富的實踐基礎。在我國,檔案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但完整意義上的檔案工作歷史并不長。在紙張未面世以前,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已經發現對某種既往活動信息存在著需要。而這種信息總是附著在龜甲、獸骨、縑帛、鐘鼎、竹木、石頭等物質之上,的他們將這些信息保管起來備以查考,形成了我國最早的檔案工作。唯物論的認識論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各項實踐的產生總是根據人類社會需要的緩急程度,按先具體后抽象的秩序決定先后的。當人們的感性認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上升為理性認識,再經過實踐的驗證,又逐步將零星的理性認識系統化,最終形成一門學問。由于早期檔案信息與載體的不可分離性,給人的錯覺是檔案就是一種物體,因而在檔案工作中往往把一些本來屬于文物范疇的東西(如產品樣品、古錢幣、鐘鼎、名人遺物等)當作檔案。按照人類的認識總是從具體到抽象的規律,人們把這些特殊物作為檔案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它們畢竟從某個側面記錄了人類某方面社會活動的信息,是對某種歷史的反映。不過這些物質只能間接地反映出某種信息,而不是對信息的直接記錄,不具有檔案的本質屬性。
3、《檔案法》和《文物保護法》概念交叉造成的矛盾。在《檔案法》中是這樣表述的:“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而《文物保護法》第二條規定“受國家保護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物包括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和壁畫,具有重要意義的建筑物、遺址、紀念物、歷史上各時代的珍貴藝術品、工藝美術品;反映各時代社會制度、生產、生活的代表性實物,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具有科學、歷史、藝術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在這兩個法律中“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具有科學、歷史、藝術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和“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概念交叉,客觀上造成人們無所適從。《檔案法》第三章第十二條規定:“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保存的文物、圖書資料同時是檔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上述單位自行管理。”《檔案法》這一規定實際上是對檔案的雙重身份作了肯定。同時也承認目前對于這部分具雙重身份的檔案的實體管理與實體歸屬問題暫無比現行做法更好的方法。可是由于檔案和文物這種在現實中的交叉重復關系,勢必將會隨著社會的發展,檔案事業和文物事業的發展,而在二者之間產生一系列的矛盾。
二、“實物檔案”概念不成立
顧名思義,實物檔案即具有檔案屬性的實物通過收集整理而轉化成的檔案。實物能否成為檔案中的一個門類呢?唯物辯證法認為,決定一事物與它事物的區別的不在于它們的外形特征,而在于它們內在的本質的特征。石頭、鐵、煤炭、水晶之所以是不同的事物,是由于它們內在的元素結構不同,而表現出的不同形態。從理論上講,實物檔案的內涵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實物,一個是檔案,客觀具體是它的外在特征,原始記錄性是它的內在特征。實物之所以不能成為檔案,關鍵在于這些實物不具有檔案的本質屬性?原始記錄性。我們知道,檔案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記錄,是人們辦理完畢保存備查的一種文件,它是融原始性與記錄性于一體的特殊事物。所謂原始性,就是說它是人們在社會實踐活動的當時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事后編纂和加工的。所謂記錄性,自檔案學誕生以來,檔案界研究的“記錄”無一例外的是指狹義的記錄,即用文字、符號和圖像等記錄工具直接將人類社會活動信息記錄在特定載體(如紙張、膠片、磁盤、光盤等)上,而人們只要掌握了識別這些文字、符號和圖像的工具就能獲取其中的信息。而實物檔案具不具備這些特征呢?不可否認,檔案館、室所收藏的實物,(包括古代用來調動軍隊的虎符,封建帝王賜予的尚方寶劍)也許具有原始性,并能傳遞給人們人類既往活動的信息,但它并不能成為檔案,理由是它不具有狹義的“記錄”性質,不是通過文字、符號和圖像等記錄手段直接將信息記錄于特定載體,反映某一行為的全過程,而是通過某事物的形態與結構反映某種行為的結果,人們只能通過對實物的觀察、分析和推測去獲得某種深層次的信息。(如法國的比薩斜塔,我們僅憑外觀只能獲得塔的結構、形狀和傾斜角度等信息,如果有檔案可查的話,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建造年代,還可以了解到塔傾斜的原因,弄清它是巧奪天工的杰作,還是地殼變遷的結果)。有人認為,實物檔案是用一種具體的、直觀的形式記錄信息。這事實上是將狹義的“記錄”廣義化了,按此觀點推論,上至天上的云彩、星星,下至地下的巖層、礦石,無不從一定角度記錄一定的信息,它們如果都可以成為檔案,那世間的萬事萬物也就都是檔案了。這樣一來,文物不就消亡了?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來分析實物能不能成為檔案。在這些年開展的關于實物檔案的討論中,不少的人認為,實物檔案是檔案的一種,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他們的理論及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關于檔案概念的界定:“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由此得出結論:檔案具有多種形式。按照檔案信息的表現形式,檔案可分為紙質檔案、聲像檔案(現代又產生了電子檔案)和實物檔案等。這些同志認為檔案部門收藏的古代的印章、刻有文字的碑匾、獎杯、獎牌、證書、錦旗、古幣、古服飾、歷史名人用物、產品樣品等都屬于實物檔案之列。其實這是對檔案概念的一個誤解。上述物體中古錢幣、古服飾、歷史名人用物無論怎么講都屬于文物,印章、碑愿、獎杯、獎牌、證書、錦旗雖可以作為檔案保存,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說它就是實物檔案,因為作為檔案部門要保存的僅僅是這些物體上記錄的某種信息而不是物本身,只不過該信息與該物體無法分離而已。假若是一塊刻有重要信息的石碑,我們不但不需要這塊石頭有多厚重,反而希望它越薄越好。由此可見,此類檔案只是載體的不同,是該與紙質檔案、電子檔案相提并論的金石檔案、縑帛檔案,而不能認為是實物檔案。
三、“實物檔案”帶來了理論與實踐的混亂
眾所周知,檔案是指辦理完畢保存備查之文件(用文字、數字、符號、圖象將信息直接記錄。到紙張、磁帶、光盤等載體的文書材料)。“實物檔案”造成的理論混亂,首先是它打破了檔案構成體系的基本要素——“文件材料,把它擴展到了自然界所有能反映一定信息的客觀物質。其次,是把狹義的采用特定記錄手段的直接“記錄”,變成了廣義的某種行為結果的間接“記錄”。其三,是忽視了信息存儲方便、傳遞快捷、復制簡單和資源共享等特點,混淆了實物反映信息與書面記錄信息的界限。其四,違背現行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明確規定“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著名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建筑物、遺址、紀念物;歷史上各時代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等屬于文物范疇,而我們硬要把具有紀念性質的獎證、獎杯和生產企業的生產樣品作為檔案。其五,導致“兩法”打架。《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把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界定為檔案,自然這些歷史記錄應該包括“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則界定“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等”屬于文物,很顯然它包括了“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的一部分。理論上的混亂,必然引起實踐上的混亂。在實踐中,檔案館室存文物,文物館室存檔案,文物搶檔案,檔案搶文物,互不相讓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尤為典型的是陳景潤的“1十2”手稿,明明是珍貴的科技檔案卻被征集到了文物部門;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契約”、東京大審判的判決書的底稿、中國“人才一號”的交流協議等,這些無論從廣義的角度還是狹義的角度理解,都屬于檔案的東西,卻偏偏保存在博物館或圖書館。
四、關于檔案與文物界定之設想
《檔案法》明確指出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在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縱觀世界百年檔案定義,無不以“文件材料”、“原始記錄”、“非現行文件”、“書寫文件、圖片、印刷品的總合”、“留待參考之文書”、“文獻記錄”等作為檔案的屬概念。可見,自古以來我們講的檔案就是指的用文字、圖表、聲像等特定手段記錄信息的特定載體。《文物保護法》明確指出: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著名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建筑物、遺址、紀念物;歷史上各時代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反映歷史上各時代、各民族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屬于文物受國家保護。對文物的解釋,《辭海》是“遺存在社會和埋藏在地下的歷史文化遺物”,《漢語大詞典》是“歷代相傳的文獻古物”。從這些定義中,我們得到什么樣的啟示呢?1.在物質形態上,檔案是各種不同形式的文件材料;文物則是有歷史、藝術、科學、史料價值,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代表性的實物(如長城、天壇、黃帝陵、黃道婆的紡車、賀龍起義的菜刀)。2.在對信息的記錄方式上,檔案是用文字、數字、圖表、聲像等記錄手段直接記錄信息,只要利用者掌握了識別這種記錄符號的本領,就能夠獲得其中的信息;文物則是用某種物質形式間接記錄信息,要了解該事物的全部信息必須借助一定的媒介(如書籍、影視等),這就是博物館、陳列室為啥要用解說詞和解說員的道理。3.從內容涉及的廣度和深度看,檔案記載著人類社會活動各個方面的信息,可以記錄下事物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具有一定深度;而文物只能記錄事物本身的結果的信息,人們只能通過物體信息去推論相關的社會信息。4.檔案信息具有方便存貯、易于傳遞等特點,而文物保管難度大,傳遞、運送不方便。由此,本人認為,檔案的落腳點應該在“文”上,即用文字、數字、圖表、聲像等記錄手段記錄著信息的紙張、磁帶、光盤等文件材料。文物的落腳點應該在“物”上,諸如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物,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代表性的今物。對于那些記錄有信息的物體,判斷它屬于檔案還是屬于文物,就是要看它的文字意義(信息價值)大于物還是物的意義大于文字意義(信息價值)。
五、如何看待檔案館、室和博物館收藏具有交叉屬性的實物
目前,我國的一些檔案館室收藏的被稱做檔案的實物,大致可以分為3種類型:一部分屬于文物(如古幣、古服飾、歷史名人用物等);一部分屬于佐證物(如獎杯、獎牌、產品樣品等);還有一部分屬于文件材料“(如證書、錦旗、牌匾等)。第一種情況顯而易見,無需贅述。為什么要把獎杯、獎牌、產品樣品作為佐證物而不作為檔案呢?因為獎杯、獎牌是通過評定或比賽而決出來的,這種評定、比賽的書面記載或聲像記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檔案,而獎杯獎牌只不過是給勝利者的一種紀念物,如果有價值的話,將來可能轉化為文物;至于產品的樣品,它只是某一設計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的佐證物,真正的檔 案應該是知識形態的產品設計文件。至于有些企業把本廠的產品也當作實物檔案加以保存,這更是不可取的。因為我們要了解某種型號的產品,完全可以通過相應的圖紙,而這些圖紙已作為科技檔案加以保存了。被“實物檔案”論者認為是實物的另一部分是證書、錦旗、牌匾,其實應該歸入文件材料之列,道理很簡單,它們的實質不在于物的意義而在于文的意義,“物”只是“文”依托的載體。證書漂亮的外殼,錦旗美麗的形式,匾牌堅硬的質地,都只是對內容的包裝,都只是文件材料的載體不同而已。由此,筆者以為,檔案館室所收藏的實物,除一部分屬于文物外,另一部分是對檔案作補充和佐證的物質,只具有檔案室保存的資料的性質,還有一部分則是待殊載體(如金屬、石料)的文件材料,也只能稱為“金石檔案”,或統稱為“其它載體檔案”,決不該稱什么“實物檔案”。
六、否定“實物檔案”的意義
綜上所述,正如有的同志認為,“實物檔案”這個概念在思維領域違背了人類對物質世界認識的規律,在檔案學理論上違背了檔案分類規則,在檔案工作的實踐中起著誤導作用。從檔案的歷史淵源上講,它不包括實物,從現代檔案工作的狀況看,它仍不該包括實物。我們否定“實物檔案”,不僅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首先,將正本清源,真正劃清檔案與非檔案的界限,建立一個準確的“檔案”概念,推進檔案學理論建設,從而更加有效的指導檔案工作的實踐。其次,便于檔案工作者把握檔案館、室工作的重點,進一步做好檔案館室的業務工作;第三,明確劃分檔案部門與文物部門的職責,理順管理關系,建立一個職、權、責關系明晰的社會分工體系,促進檔案事業與文物事業共同發展。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