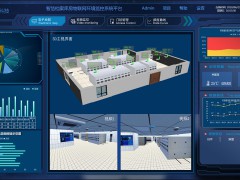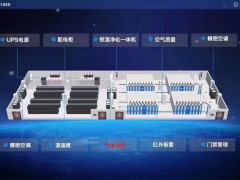二、司馬遷與《史記》
1、司馬遷生平
司馬遷,字子長,公元前145年(漢景帝中元五年)生于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縣)。他生長的時代,正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位學(xué)識淵博的太史令。漢代太史令的職務(wù),主要是管理國家典籍,還要精通天文歷算、通曉古文經(jīng)傳和諸子百家學(xué)說。正如司馬遷在《自序》中所說:“天下遺文古事,靡不集畢集太史公”[i]。有了這樣好的條件和環(huán)境,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積累了多方面的知識,為日后繼承父業(yè)打下了基礎(chǔ)。
為了增廣見聞,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從二十歲起開始徒步游歷名山大川。據(jù)其《自序》所記:“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凝,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以觀孔子之遺風(fēng),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這次遠游,足跡遍及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qū)和今山東、河南等地。在游歷中,司馬遷除了縱觀山川形勢風(fēng)土民情以外,還考察了歷史遺跡,采集了大量重要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所謂“上會稽,探禹穴”,便是到了浙江會稽山,探訪了傳說中的夏禹遺跡。司馬遷“北涉汶、泗”,到了孔子出生地后,盤桓良久,體會到了孔子教化感人之深。特別是在彭城、豐、沛一帶漫游時,司馬遷深入探訪了漢初的史跡,他不僅從民間得知了漢高祖劉邦在鄉(xiāng)間好酒色的故事,還對這些人屠狗賣繒的生活,作了仔細(xì)的調(diào)查,參觀了蕭何、曹參、樊噲等的葬地,掌握了大量極豐富的實際資料。
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東巡,登泰山舉行封禪大禮。司馬談因病未能成行,賚志以終。臨終前,交待司馬遷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fù)為太史,則續(xù)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tǒng),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ii]司馬遷垂淚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司馬談去世后三年,即元封三年,司馬遷被任命為太史令,這一年他38歲。
司馬遷當(dāng)上太史令以后,有機會飽覽 “石室金匱”之書,也就是皇家藏書庫中所藏的各種典籍文書和檔案資料,這對他“悉論舊聞”的工作無疑具有很大的便利。但是司馬遷剛?cè)翁妨顣r,并沒有馬上著手于史書的編纂,而是受漢武帝之命,主持了“太初歷”的制訂。漢初建國后,一直沿用秦的《顓頊歷》,以致出現(xiàn)很多混亂。太史令的職責(zé)之一就是掌管歷法,司馬遷繼任后,上書建議對現(xiàn)行歷法進行修改。于是漢武帝便命司馬遷主持修訂,司馬遷與十?dāng)?shù)名歷法家經(jīng)過努力推算,制定出一個以正月為歲首的新歷,即《太初歷》,亦即今天通行的“夏歷”(農(nóng)歷)。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歷工作結(jié)束以后,司馬遷就開始了他的偉大的寫作計劃,這一年,他42歲。過了五年,他為了李陵敗降匈奴的事說了幾句直話,觸怒了武帝,以為他有意誹謗李廣利,[iii] 替李陵開脫,便把他逮捕入獄,判處死刑。按照漢律,判處死刑者,有兩種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納錢贖罪,另一種是受“腐刑”。前者司馬遷辦不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iv] 在這種情況下,要活下去,只能接受“腐刑”。對此奇恥大辱,司馬遷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著作尚未完成,“草創(chuàng)未就,適會此禍”,想到許多古代前賢,都是在逆境中發(fā)憤著作:“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v] 為實現(xiàn)平生的著作理想,司馬遷遂決計以古先賢為榜樣,“受極刑而無慍色”,……到天漢五年(公元前96年),司馬遷出獄不久,被任命為中書令。漢中書令名義上地位比太史令為高,實際上只是“閨閣之臣”,與宦者無異。這種處境,使司馬遷常常感到一種恥辱,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vi] 但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夠繼續(xù)他的著作。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他在給友人任安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著作已經(jīng)基本完成的消息:“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紿,稽其成敗興壞之紀(jì),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jì)十二,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vii] 這時他大約五十四、五歲。此后,他的事跡就無從查考了,卒于何年也無從確定,大概逝世在武帝末年。
2、《史記》一書的材料來源
司馬遷《史記》完成以后,全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其記事內(nèi)容,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包括了上下三千年的歷史,無論其涉及時代之遠,包含范圍之廣,史學(xué)價值之高,藝術(shù)影響力之大,《史記》都是空前的。司馬遷能夠?qū)懗鲞@樣一部貫通古今三千年的偉大著作,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掌握了極為豐富的歷史材料。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材料來源,大體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充分利用當(dāng)代與前代保存下來的檔案文書。我們知道,自西周以來已經(jīng)逐漸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官方檔案文書的收藏與保管制度,周代的太史、秦漢的太史令的專職之一就是負(fù)責(zé)保管“石室金匱”中所典藏的檔案文書和國家典籍。在諸侯爭霸的戰(zhàn)爭年代,戰(zhàn)勝的一方也十分注重對典籍的搜集,如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時,“悉內(nèi)(納)六國禮儀”[viii]。到了天下并起亡秦時,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ix] 這一類的檔案公文材料,均屬秘藏,非一般人所能見到,而司馬遷因職務(wù)關(guān)系,在撰寫《史記》時,充分地運用了這些材料,尤其是有關(guān)秦漢之際的歷史,許多內(nèi)容都是依據(jù)檔案材料寫成的,如《曹相國世家》、《樊噲列傳》等所記戰(zhàn)功,若是沒有檔案材料可資依據(jù),要寫出那樣精確的數(shù)字是很難想象的。又如《三王世家》就曾全錄封策原文,保存了“漢廷奏覆頒下施行之式”。
二是廣泛收集、充分利用各種圖書文獻。漢代建國之初,十分留意于圖籍的收藏。漢武帝也十分喜歡搜羅圖書,曾數(shù)次下令全國,征求圖書,并在宮里設(shè)了幾個藏書的地方。經(jīng)過歷朝最高統(tǒng)治者的訪求征集,漢皇家書庫得以大大充實起來,即所謂“天下遣文古事,靡不畢集”。這些書籍,按司馬遷的話來說,是“六經(jīng)異傳”、“百家雜陳”,數(shù)量絕非鄭樵“七、八種”所能包容得下。凡《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圖書,除晚出者外,漢武帝時期的皇家書庫中應(yīng)當(dāng)都有收藏。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對這部分圖書,具備利用上的諸多便利。此外,司馬遷還十分注意對各種圖書文獻,包括野史雜記之類書籍的搜集。從司馬遷《史記》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到他大量利用圖書文獻的蹤跡,如《大宛列傳》中有“《禹本記》、《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是司馬遷讀過《禹本記》、《山海經(jīng)》之證;又《衛(wèi)世家》“贊”稱“余讀世家言”,說明時有《世家》一書;又《伯夷列傳》開頭便提出“其傳曰”來總起下文,可知司馬遷當(dāng)時是看到伯夷、叔齊的舊傳后才動筆寫作的。由此可知司馬遷除了充分利用了檔案材料外,還將當(dāng)時所能看到的所有典籍甚至是雜書野史,作為自己撰寫著作的材料基礎(chǔ)。
三是重視運用親身見聞和實地調(diào)查的材料。這種由實地采訪所得的材料,其價值往往勝于有形的文字記載,它不但可以補充文字史料的不足,訂正記載中的謬誤,而且可以加深對真實歷史的了解程度。如司馬遷初到淮陰時,聽人家說:韓信年少時,志向很大,他母親去世時,雖無以為葬,卻不顧一切尋到一處墓旁可住萬家的葬地。司馬遷聽后,就親自去參觀了韓信母親的墳?zāi)梗笮牌溲圆惶摚由盍怂麑n信的認(rèn)識。如在豐、沛等地游歷時,司馬遷實地調(diào)查了漢高祖劉邦起事前的活動情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如呂公遷沛時,客人出不到一千賀錢的,便坐堂下,劉邦詐言賀錢一萬,其實不名一文;劉邦服役咸陽時,別人都出三錢,蕭何卻出五錢,所以后來以蕭何為第一功,封賞最厚等等。這些材料,決非官方文書檔案所能記載,只有通過實地調(diào)查與征集,才能得到這些生動的第一手材料。司馬遷將這些材料運用于人物傳記寫作,使得秦漢之際的人物能夠?qū)懙描蜩蛉缟4送猓抉R遷在游歷時,留意考察名山大川、軍事要隘形勢,所以《史記》中有關(guān)秦漢之際大小戰(zhàn)役的描寫,使人有親臨其境之感,正如顧炎武所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了然。……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后代書生之所能幾也”。[x] 司馬遷之所以能夠如此準(zhǔn)確地敘述戰(zhàn)爭形勢,與他在游歷時期的細(xì)心觀察、調(diào)查是密不可分的。
司馬遷在掌握了豐富的材料后,并沒有為材料所役,隨便征引采用,而是經(jīng)過認(rèn)真仔細(xì)的比較、考訂與審核,決不輕信輕用,即使是官方檔案也是如此。對古書上所記的怪異之說,更不隨聲應(yīng)和。正是由于司馬遷在處理史料上的嚴(yán)肅詳審的態(tài)度,所以《史記》才為后人一致公認(rèn)為“實錄”。
3、《史記》對檔案編研工作的啟示
司馬遷的《史記》是在研究古代所有文獻材料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自己的剪裁熔鑄,著成《史記》這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全書運用本記、表、書、世家、列傳等五種體例,把上下三千年,縱橫數(shù)萬里的歷史、人物以及各種社會活動、人文地理、風(fēng)土民情有機地融會在一起,相互配合,互為補充,聯(lián)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鄭樵說:“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xué)者不能舍其書,《六經(jīng)》之后,惟有此作。”[xi] 清趙翼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xii] 這都是說司馬遷創(chuàng)立的這種全新的紀(jì)傳體編纂方法,對后世史學(xué)家的巨大影響。即使在今天檔案編研工作也可以從司馬遷《史記》中得到處許多有益的啟示。
一、廣泛搜集材料,審慎取舍,注重歷史真實性。前已提及,司馬遷十分注重對材料的廣泛搜集,其所搜集的材料包括許多先秦經(jīng)籍和秦漢之際某些人寫的著作,司馬遷在寫作時,大量采用了這些資料,但是他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并不是原搬照錄,而是經(jīng)過仔細(xì)的爬梳剔抉,并對照他從實地考察得來的材料排比鑒別,最后用生動的語言連綴成篇。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就是:“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這些“放失舊聞”、“《六經(jīng)》異傳”、“百家雜語”經(jīng)過司馬遷的考訂與整理,就成為較可靠、系統(tǒng)的內(nèi)容。
二、貫通古今,條分縷析,按照編撰目的形成系統(tǒng)化的編撰體例。要把經(jīng)過精心挑選的大量材料組織成篇,就要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對其進行編排整理,這就是編纂的體例。司馬遷在撰著時,采用了五種體裁:“本紀(jì)”是年代的標(biāo)準(zhǔn),從五帝至漢武帝,各依時代為先后。“表”是全書的綱領(lǐng),從《三代世表》到《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也是依時代先后編列的。它和本紀(jì)互為補充,彼此對照。“世家”與“列傳”主記人物活動,前者多為紀(jì)傳合體的國別史,后者為各類人物傳記。“書”是關(guān)于風(fēng)土山川名物制度的記述。五種體裁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如“紀(jì)”與“傳”是構(gòu)成全書的經(jīng)緯,“紀(jì)”以時代先后敘述帝王活動,“傳”以人物記載為主,分別組織安排材料,相輔相成,使全書組織系統(tǒng)條理,秩然不紊。
司馬遷對每一種體裁中有關(guān)材料的處理,也經(jīng)過了精心的通盤籌劃。如列傳七十篇,份量占全書的絕大部分,材料最多,處理難度也最大。司馬遷按照“以類相從”的原則,分別不同情況進行處理。對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如秦相商鞅、魏公子無忌等,均單獨列傳。對行事相類的人物,則合為一傳,如刺客、循吏、酷吏、儒林、游俠、佞幸、滑稽、日者、貨殖等列傳,即為類傳。還有二人或三人的合傳,或按身份劃分,如《管晏列傳》因管仲、晏嬰同是齊國的良相而合為一傳;或由學(xué)術(shù)相同而合,如《孟軻荀卿列傳》中孟子、荀子同為儒家而合為一傳;或據(jù)其行事特點而合傳,如《屈原賈誼列傳》便取其有共同的心境和遭遇而合傳等。每一種安排,均有其獨到的見解。對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將道家老子與法家申不害、韓非子合為一傳的做法,后世很多人不能理解,以為是司馬遷自毀體例。其實,對這一點,司馬遷在書中交待的很清楚,他說:“申子之學(xué),本于黃老”,又說韓非子“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xué),而其歸本于黃老。”[xiii] 這就指出了法家之學(xué),是原于道家,司馬遷把老莊申韓合成一傳,是從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來看問題的。高度地體現(xiàn)了組織史料的系統(tǒng)性。
在對具體材料的編排上,司馬遷也十分審慎。若遇一段材料,即可以放在甲篇,也可以放在乙篇時,就要反復(fù)斟酌,衡量輕重后再決定取舍。如《尚書洪范》,相傳是箕子對周武王討論“天人之道”的一段話,照理可以收入《周本紀(jì)》,但司馬遷在《周本紀(jì)》只提到“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丑,故問天道”,而沒有舉出問答之辭。這不是他不采《洪范》,而是將《洪范》全文收入《宋微子世家》,因為宋國是殷代后裔的緣故。由此可知,司馬遷對材料的處理,是經(jīng)過了認(rèn)真的推敲考慮的。對已經(jīng)放在某篇的材料,遇著與此有關(guān)聯(lián)時,便采用“互見”的形式予以提示說明。如《秦始皇本紀(jì)》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孝文本紀(jì)》說:“事在呂后語中”;《蕭相國世家》說:“語在淮陰侯事中”;《絳侯周勃世家》說:“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等等。這一類“事在某篇”、“語見某篇”的交待,通篇盡見,這種“互見”方法不僅避免了各篇間的重復(fù)記載,節(jié)省了不必要的繁文,而且易于讀者將全書作為有機整體閱讀理解。司馬遷在材料處理上所具有的系統(tǒng)縝密的方法值得借鑒。
三、實事求是,疑則存疑、疑則闕焉的科學(xué)態(tài)度。司馬遷在對材料的處理上,無論是書面材料,還是親自調(diào)查到的見聞,從不率爾輕信,而總是經(jīng)過一定分析鑒別的。他對傳說中的“五帝”的世系,就曾將書面材料同實際調(diào)查的材料放在一起,進行詳細(xì)的考察,而以“不離古文者近是”作為結(jié)論。[xiv]對于那些不能確定的記載,他絕不武斷,不曲解,而是采取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疑則存疑。如關(guān)于老子這個人的姓名、年齡、籍貫,在漢初已經(jīng)弄不清楚。司馬遷在修《老莊申韓列傳》時,將當(dāng)時幾種不同的說法,用“或曰:……”,“或……”的形式加以載錄,最后用 “世莫知其然否”的懷疑口吻來表明自己也不知道,并不因為自己有所不知而強取一說,作為掩飾。對于墨子的時代,司馬遷因不能肯定,就說:“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jié)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xv] 這一類寫法,都是采用闕疑的方法,兼采眾說,留待后人判斷。
對于那些傳聞異說,司馬遷的態(tài)度更為審慎,“神農(nóng)以前,吾不知已”[xvi],自己不知道的,就不隨便寫;“至《禹本紀(jì)》、《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xvii],古書所記的奇談怪物,未經(jīng)過考證,也不隨聲應(yīng)和。司馬遷還注重對史料的考證鑒別,如對“學(xué)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的歷史,他經(jīng)過認(rèn)真的考證,認(rèn)為“其實不然”,“武王在豐,使召公復(fù)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fù)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及至犬狨敗幽王,“平王立,東遷于洛邑,辟戎寇。”[xviii] 這便論定了周居洛邑,是在幽王以后。總之,司馬遷在《史記》中采用的編纂原則和方法以及實是求事的科學(xué)態(tài)度,為今天的檔案編研工作留下了許多有益的啟迪。
[i] 《史記·太史公自序》
[ii] 《史記·太史公自序》
[iii] 李廣利是漢武帝劉徹寵姬李夫人之兄,當(dāng)時為貳師將軍,是李陵的主帥,后來也投降了匈奴。
[iv] 司馬遷《報任安書》
[v] 同上。
[vi] 同上。
[vii] 同上。
[viii] 《史記·禮書》
[ix] 《史記·蕭相國世家》
[x] 顧炎武《日知錄》卷26《史記通鑒兵事》。
[xi] 鄭樵《通志·總序》
[xii]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1《各史例目異同》
[xiii]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xiv] 《史記·五帝本紀(jì)》
[xv]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xvi] 《史記·貨殖列傳》
[xvii] 《史記·大宛列傳》
[xviii] 《史記·周本紀(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