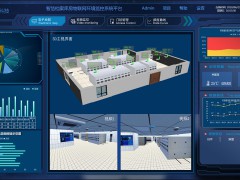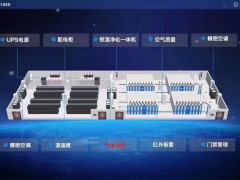二、校勘學與檔案編研
“校勘”二字,古稱“校讎”、“讎校”,今稱為“校對”,即對書面文字材料進行的補闕訂偽,刪除重復,條理篇目的工作。
(一)校勘學起源與作用
校讎工作,起源很早。《國語·魯語下》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正考父是周末宋國大夫,即孔子的七世祖,曾從事《商頌》的校對工作。孔子在整理《六經》時,也十分注意于校勘工作。《呂氏春秋·慎行》:“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子夏是孔子的學生,受孔子的影響,熟悉書籍中的錯訛現象,故能指出“三豕涉河”是“已亥涉河”之誤。到了漢代,劉向父子進行的大規模的整理文獻典籍的工作,形成了整理校勘圖書的方法。后人在此基礎上加以總結,逐漸形成了系統的校勘學的理論和方法,使校勘學成為了一種專門的學問。
古代文獻傳世久遠,難免存在許多錯誤。尤其是雕版印刷術盛行以前,所有文字材料基本上都是靠手寫,容易抄錯或脫落一些字。而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后,在刻印中出現字體缺謬,語句脫落,衍文增句等等,也屢見不鮮。如果遇到錯誤的本子,以訛傳訛,不僅會影響到對文字的理解,有時還會造成很不好的后果。《顏氏家訓》中記載了兩件事,其一為:“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后尋跡,方知如此。”將“芋”誤為“羊”,鬧了個大笑話。其二為:“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頊’當為‘許綠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作‘專鹮’爾。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這是一個因誤字而致誤讀音的事例。可見,因字的筆畫增一筆或減一筆,都會直接改換文句的原意,影響到內容的真實性。
如果錯訛的是與古代名物制度有關的文字,就會引起很多混亂,嚴重的會影響到對整篇文義或某項制度的理解。《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左學,養庶老于右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這是古代相傳虞夏殷周四代養老制度的一段記載。“上庠”、“下庠”“東序”……等都是古代學校的名稱。《北史·劉芳傳》劉芳上表中所引《禮記》云:“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由此可知,在南北朝時期,劉芳所見到的《禮記》的本子,和今本不同。可以肯定“虞庠在國之西郊”一句,唐以前的舊本,作“四郊”。清代學者孫志祖根據劉芳所見舊本,訂正今本《禮記》的誤字。“《禮記·王制》:‘周人養國老于……。虞庠,在國之西郊。’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小學,豈應偏置于西郊乎?《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其為四郊之偽無疑。”[①] 孫氏這段考證,確實是很有見地。這是因錯一字而產生的誤解。
有時古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無意脫一字或增一字,會直接影響到內容的真實性,并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爭論和糾紛。如關于漢初《古文尚書》的發現,就有一段公案。《漢書·藝文志》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學官。”孔安國是孔子后裔,《史記·孔子世家》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在寫《史記》時,稱孔安國早死,如何見及巫蠱之難?這是一個疑案。清初學者閻若璩在讀荀悅《漢紀·成帝紀》時,發現上面載有“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在“孔安國”下有一“家”字,據此可知是《漢書》脫漏了此字。問題遂迎刃而解。
由此可見,經過長期的輾轉傳寫和刊刻,古代流傳下來的文獻材料,不但魯魚亥豕,錯字很多,甚至連個別段落章節都有顛倒或脫落的現象。因之對之進行校對是極為重要的一項工作。
(二)校勘學的方法
關于“校勘”,或稱“校讎”,劉向曾說:“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②] 這種方法是兩人合作,一個人念書,一個人拿著本子仔細對看,遇到偽字誤句,便要仔細推校,尋找出問題的所在。現在的出版部門的校稿,則是一個人用一底本與校本來進行校對,其工作方法與原理則是相同的。因此,在校勘時,選一個好的底本是保證校勘質量的首要條件。其次應多儲副本,廣搜博采;盡量搜集古本,時代愈早便愈可靠。還要利用甲骨刻辭、金石銘文、敦煌寫本等材料作為校勘的重要依據。
陳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補釋例》中提出的“校法四例”,對前人的校勘方法進行了總結歸納,被認為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其四法為:
對校法:即以祖本與別本對校,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通過對校,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先用此法。對校法是基本的校書方法,通過校對比勘,找出相互間的差異,以了解各本的異同情況。
本校法:以本書前后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即根據原書的體例、綱領,以及作者或傳鈔者的書寫習慣等,對全書通有的錯誤進行校勘。
他校法: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或后人引用者,則以所引之書校之。此法主要針對引文的校對,遇有書中引用別書的內容時,則找出有關書籍進行校對,撲克其所引用的文字是否與原文相符。
理校法: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用此法。但用此法需具有較高學識,否則率爾操觚,后果不堪設想。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這種方法是校勘中的最難的一種,即不專憑書本的對校,而是用歸納、演繹邏輯的方法來考證古書中的錯誤。即將古漢語句、文法、音韻、訓詁以及名物制度等的知識加以綜合地運用,來分析辨別真偽是非。
但是,無論哪一種校勘方法,都須要具備一定的文字基礎。因為校書本身就是一種勘正文字的工作。如果對漢字的結構、音讀、語法、用法等方面的知識沒有一定的了解的話,是很難做好這項工作的。
(三)校勘學與檔案編研
整理編纂檔案文獻,同樣也有一個校勘的過程。其一是對檔案材料文字的加工,即在抄纂過程中發生的“辨文識字”問題;其二是對文句的加工, 即“讀”的問題“讀”即“句讀”,通俗的講法稱為“標點”;其三是要解決檔案材料中的錯訛問題,即如何進行辨偽糾謬。
句讀與標點
一般古代文獻,絕大部分都沒有圈點和句讀,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古漢語語言現象。所以《禮記·學記》中談到古代教育程序和檢查學習成績時說過:“一年,視離經辨志。”鄭玄注云:“離經,斷句絕也。”也就是說,檢驗學習的進步與否,先要看他會不會讀書斷句。古人著書不加句讀,句讀是讀書人的基本功,故有“學識何如觀點書”之說。
漢代以來,人們為了自己讀書或為便于初學者讀書,在書中加上句讀標志,如用“〇 ”或“√”,除個別地方用作章句號外,一般用來斷句。盡管已有句讀的符號,但古人在著書寫書時,習慣上仍不加標點。但是寫書不加句讀,給讀書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因誤讀而導致的錯誤也經常出現。《朝非子·外儲說左下》記載:“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原來,“夔有一足”是一個緊縮的復句,四字應作二句讀,魯哀公把這四字連讀,得出夔只有一只腳這樣不合理的結論。
新文化運動以后,出現了新式標點符號。1919年,胡適等人提出《請頒行新式標準符號議案(修正案)》,列舉了19種標點符號及其用法。第二年教育部通令全國施行,但仍只局限于白話文。政府機構中的公文案牘基本上仍是通篇一貫到底,中間不加任何標點間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規定了公文必須使用標點符號,使公文檔案的無標點現象有所改觀。但各部門在擬撰公文時,并沒有規范統一的標點方法,有的只有“、”和“。”兩種,有的則是一逗到底,或“,”、“。”混淆,當點不點,當斷不斷,使用情況比較混亂。檔案文件中無標點公文及不規范標點符號的大量存在,成為檔案整理工作的一大障礙。
魯迅先生說過:“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于遲疑。”[③] 可知標點句讀并非易事。不僅需要平時知識的積累,還要掌握一定的句讀標點的方法。
標點古書與標點近現代檔案史料一樣,首先要從認字辨義開始。所謂認字,就是不僅要認識書中的每一個字,還要結合上下文搞清每個字在句中的準確含義。漢字屬于表意文字,一字多音,一字多義的現象極為普遍,同是一個字,在不同的句子里可能有不同的讀音、不同的形體、不同的含義。如果不仔細聯系上下文進行分析,就拿起筆來斷句,很容易產生錯誤。如《左傳·成公二年》“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句,有人點為:“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誤。這里說綦毋張站在左邊右邊,韓厥都用手肘制止他,讓他站在后面。如果把“從左右”看成是綦毋張說的話,那么“皆肘之”就無所系屬,上下文的意思都說不通了。正確的標點應是:“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又如“希查照協助賜予代為調查俾利進行”一句,是屬于檔案中比較常見的公文套話,有人則點為:“希查照協助賜予,代為調查俾利進行。”顯然標點者并未搞清“賜予”與“俾利”的用法,前者為祈使語,后者為承接語,意為“以便于……”,應屬下句。
其次,要了解語法結構和一些特殊的句式用法。檔案中的公文用語有特殊的用法。如起首語:有“某某鈞鑒、某某公鑒”等,為上行或平行起首語,表示對受文者之稱謂,其下自應用冒號“:”;而“敬稟者、逕啟者”之類,同樣是起首語,但卻是發文者的自稱,故其下應用逗號“,”。又如,舊式公文中的層層照轉文句,常見的有“奉……令開”、“準咨開”、“函稱”、“函開”等,其所“開”、“稱”之文句均屬轉述它文之語,其下須標冒號,以作提示。如;內務部為咨行事。準國務院函開:準司法部函開:準江蘇省高等法院呈稱:“近來日貨走私又復激烈,……請根本取締。”等語。上文內政部咨行之事,是國務院、司法院、江蘇高法這三個遞進的發文單位轉述的同一內容,這里層層照轉的文句均用冒號提示,表示公文內容的層屬關系,因而可以使公文表述的意思一目了然。此類引據語式,必須弄清其承轉關系,才能確切加以標點。
再次,標點檔案史料,要熟悉有關時代的人名、地名、職官及名物制度等等,否則極易出錯。如某處整理公布的《胡漢民致李曉生函》中,文中有“毅鶴晚兄鑒:”字樣。誤。此函為胡漢民致何世楨(字思毅)、陳群(字人鶴)、李曉生三人之函。此處應為“毅、鶴、曉兄鑒:” ,而上文中“晚”即為“曉”字之誤。 又如“吳煦讀申韓家言才猷敏練倚馬可待咸豐年間兵備上海兼綰藩條時江浙淪陷聯絡客將力保滬城”。此段文字雖比較容易,但也有人將其誤標為:“讀申韓家,言才猷敏練倚馬可待。咸豐年間,兵備上海,兼綰藩條時,江浙淪陷,聯絡客將,力保滬城。”致錯之因,其一為不明“申韓家言”乃指先秦諸子申不害、韓非之學說而言;其二為不明官職,指其任蘇松太道,同時負責與英法聯絡,因而文中的“兼綰藩條”與“兵備上海”皆指其所任官職及職掌。因此正確的標點應為:“讀申、韓家言,才猷敏練,倚馬可待。咸豐年間,兵備上海道,兼綰藩條。時江、浙淪陷,聯絡客將,力保滬城。”標點正確,文意自明。
由此可知,古人所謂的“學識何如觀點書”之說是多么的切中要害。因此,要正確地標點檔案史料,掌握一定的標點方法和規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還在于要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水準,多學,多看,多用,熟能生巧,庶幾才不致貽誤他人。
糾正訛誤
校讀歷史文獻,除了辨文識字、讀書斷句外,還要了解書籍錯亂致誤的一些基本規律。如因字音相近而致誤者;因字形相近而致誤者;因刊刻時串行脫落數字而致誤;因斷句錯誤而致誤;因不解典故而致誤者等等。清代學者在考據學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如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所著《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等,把古人著書的語法、詞句分析十分透徹,指出了古書中的常見錯誤。而俞樾在其所著《古書疑義舉例》中,將其校書中所發現的古書中的錯誤,歸納成三十七例:(1)兩字義同而衍;(2)兩字形似而誤;(3)涉上下文而衍;(4)涉注文而衍;(5)涉注文而誤;(6)以注說改正文;(7)以旁記字入正文;(8)因誤衍而誤刪;(9)因誤衍而誤倒;(10)因誤奪而誤補;(11)因誤字而誤改;(12)一字誤為兩字;(13)二字誤為一字;(14)重文作二劃而致誤;(15)重文不省而致誤;(16)闕文不作空圍而致誤;(17)本無闕文而誤加空圍;(18)上下兩句互誤;(19)上下兩句易置;(20)字以兩字相連而誤疊;(21)字以兩字相連而誤脫;(22)字句錯亂;(23)簡策錯亂;(24)不識古字而誤改;(25)不達古義而誤解;(26)兩字一義而誤解;(27)兩字對文而誤解;(28)文隨義變而加偏旁;(29)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30)兩字平例而誤倒;(31)兩文疑復而誤刪;(32)據他書而誤改;(33)據他書而誤解;(34)分章錯誤;(35)分篇錯誤;(36)誤讀夫字;(37)誤增不字。俞樾在這里,基本上把古書中的衍文、偽體、倒置、脫落、誤改、誤解、誤增、誤刪,以及簡策錯亂、篇章顛倒等多種現象,都完全總結出來了。
在檔案文件中,文字上的錯漏衍奪現象也所在皆是。這種情況,在戰爭年代和白區工作條件下的中共文件電報中,相對地更多一些。但是在對檔案文字進行校勘時,必須依據“存真”原則,校勘出的明顯錯、衍、脫、倒,不能直接修改,而應該一方面保留原來的字,一方面加校正的字,同時用校訂符號、注釋、校勘記等形式加以說明,使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些是文件原有的,哪些是編者校訂的。如果不加分析、注釋,逕改某些異體字、俗體字,則容易發生以錯改正的問題。如改“悤”為“匆”,改“倸”為“睬”,改“豫”為“與”,改“華”為“花”等等。其實這些字都是同義,彼此相通,只是有古體、近體、俗體等的不同而已,沒有必要加以改“正”,應盡量保存檔案的原貌。又如在黨的早期文件中,常見不規范的白話文,在有些文獻編纂物中,因不熟悉古今語言的變化,就把原來沒有錯的當作“明顯錯別字”加以校訂,有的人甚至還用符號注明原文有錯。
因此,在“糾誤”時,最忌“直改”,不經過認真的查考,就信手改動,一旦以錯改正,改變了原來的文義,很可能會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而讀者又無從察覺,造成以訛傳訛,貽害無窮。所以歷來古籍整理的專家最反對任意改動底本,并將其視之為“荒率”的舉動。
辨別真偽
檔案文獻流傳既久,本來就有衍文誤字和后人偽訛增補的地方,還有的原書已經散佚后又突然出現,如《古文尚書》的重出,便加入了后人摻入的成份。魏晉以來,造偽之風頗甚,如東漢時鄭玄遍注五經,到晉時的王肅,為壓倒鄭玄,便偽造一部《孔子家語》,以證明己說之不謬。宋代有王銍作《龍城錄》,偽托為柳宗元所作。等等。因此,偽書愈出愈多。直至近現代,造偽亦時有發生。由于書籍及檔案文件的偽造,傳說的失實,真偽不別,就會錯誤百出。如果選編的資料不可靠,就可能給利用者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因此,整理、編纂檔案文獻史料,必須辨別真偽。古代書籍與檔案史料之有真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原有古籍已經遺失,又經后人發現的。如《尚書》,西漢時有《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后又在魯共王壁中發現《古文尚書》,到東晉又有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是將原書篇章割裂,并羼入先秦諸子等的言論拼湊而成。又《竹書紀年》的發現、整理、散佚與再發現也是如此,其中都有摻偽的成份。
其二,古人未完成的著作,經后人屢次增補和竄改,不能辨別哪些是原書,哪些是后人的增補,因而是真偽參半的。如司馬遷的《史記》,其中有《武帝本紀》等十篇可以肯定是經過褚少孫增補的,但有的篇目中的增補內容并未注明為何人所補,后人便搞不清楚。唐顏師古把《漢書》二十五家注匯為一書,久經傳刻后,把各家的注都混淆在一起,如把服虔的注誤寫成應劭的注等等。近人從新發現的唐人寫本上,才明白了書中有些內容是錯誤的。
其三,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造偽。如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為造謠、誣蔑太平天國運動,而偽造的宣傳材料等。
辨偽工作,一開始便和整理檔案文獻的工作結合在一起。漢代學者即通過校書來判定書的真偽。明代胡應麟在其所著《四部正偽》中歸納了辨偽“八法”:一、覈之七略以觀其源;二、覈之群志以觀其緒;三、覈之并世之言以觀其稱;四、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五、覈之文以觀其體;六、覈之事以觀其時;七、覈之扎著以觀其托;八、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胡應麟的“八法”已經包括了辨偽工作的基本方法。其意為,遇到可疑的古書,首先檢查一下最早的目錄書以及歷代史志中,查找關于這部書的信息;其次從同時代人的著作、后世的書籍中檢查有無提及或引用該書的言論;再從文體、內容、作者姓名、傳承等方面全面了解有關的情況,最后,進行綜合的分析做出評判。近代梁啟超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談到史料鑒別方法時,也提出了辨識偽書的十二條公例,約為六點:
(1)從著錄傳授上檢查。古代有名的著作皆見于史志著錄,凡不載于《漢書·藝文志》、《隋書·經藉志》等,而后來發現的書籍,十有九皆偽。
(2)從本書事跡或所引書上檢索。如前人而引后人的事實或后代文章的詞句,則可懷疑。
(3)從文體上檢查。各時代文體不同。如《皇帝素問》有大段醫理文章,顯然是漢代人的文字。
(4)從思想淵源上檢查。各時代的思想特點,若張冠李戴,即可疑其為偽。
(5)從著錄編撰者所憑借的原始材料上檢查。如《毛詩》序襲《樂記》和《論語》的話,斷續支離,顯然有問題。
(6)從原來佚文說的反證上檢查。已佚的書,后人偽造,若從別的書發現所引原書佚文為今本所無,便知今本是偽造。
梁啟超先生所說的辨偽方法雖然是針對古代文獻的,但同樣適用于近現代檔案史料的鑒別與辨偽工作。
檔案是歷史活動的原始記錄和自然產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檔案形成過程中也會出現真偽問題。其中有同時代人的偽造,也有后代人的偽造,如太平天國檔案文件的作偽,有清朝將領為掩飾其戰敗、逃避懲罰而偽造文件者,有天地會等起義軍為借助太平天國聲勢威望,假托太平天國名義發布文告等,這些都是太平天國檔案文件中的偽作。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仍有太平天國檔案文件偽作的出現。有的是因為清末反清革命黨人為鼓吹革命而偽造,如《翼王石達開布告天下檄》,有的是后人知太平天國曾有過某文件而偽造,如發動金田起義的文告已經失傳,就有人造一篇《太平天國起義檄文》;還有的是后人誤信某事而偽造,如《天王致美國國書》,即是作偽者誤信有洪仁軒出使美國事,遂偽造此“國書”,內稱派洪仁軒出使。
當然近現代檔案文件的作偽并不僅限于太平天國檔案,民國時期也有各種原因造假的文件,如1939年汪精衛偽國民黨黨員登記表就有一半是出于偽造,其目的在于增加黨員名額,邀功請賞。
在革命歷史文件中,也存在著真偽問題。如張國燾在紅軍長征途中,另立中央,曾用中共中央名義發表過許多文件。有些史料書就把其中的某些文件錯當成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如《六大以來》中有一篇1936年1月27日《中央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支部的信》,信中的引文都是出自所謂“中央1月25日決議”,而“1月25日決議“就是張國燾偽中央發的,由此證明1月27日這封信也是張冒用偽中央名義發的。又如抗戰初期有人在武漢偽造了一本張浩(林毓英)著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路線》,書中歪曲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民主共和國口號,捏造事實,破壞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挑撥國共合作。偽造者知道張浩曾以這個題目在抗大講過課,并因某些觀點問題遭到過博古的批評,書中還故意引用了一些列寧、斯大林的講話。這種經過捕風捉影,再進行偽造,確實頗費了一番心思。對此周恩來在《解放》第36期曾做過有力的揭露。
由此可見,檔案史料與古籍文獻同樣存在真偽問題,因此,對檔案史料的辨偽也可以借鑒古籍辨偽方法。鑒別檔案真偽的主要方法有:(一)研究檔案材料的時代性。不同時代的紙張,無論在技術和品種方面,都存在有差異;(二)研究檔案文件的來源與產生過程中的具體情況;(三)分析檔案文件的歷史背景;(四)從檔案反映的史實方面來分析其真實與否;(五)分析文件程式是否符合當時的行文規定;(六)考察檔案文件的文體,是否符合當時習慣及作者身份;(七)把檔案文件與作者其他筆跡進行比較,尋找異同之處;(八)揭露其他作偽痕跡,如印鑒、語氣等。辨別檔案文件真偽的方法多種多樣,要運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綜合的考辨。
除了檔案文件存在有真偽現象,檔案內容本身也有真偽。如曾國藩向清廷匯報其部下曾國荃率兵攻陷天京(即南京)的奏折中稱:“……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尸首如麻,凡偽王偽主將天將及大小尊目約有三千余名,死于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據羅爾綱先生考證,“天京失陷后,守城軍隊一萬多人,大部分都得沖出,戰死的沒有多少。城陷以前,全城人口,連居民在內,也不過三萬人。而曾國藩卻向清廷虛報說攻破天京,殺了太平軍十多萬人。”[④] 由此可知,可能存在的檔案記載失實現象,也是檔案編研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搜輯佚文
古代書籍,存在著嚴重的散佚現象。有些書籍已經淪亡,但其名目仍載在《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以及唐宋以來的官私書目之中。這些書籍的散佚,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印刷術沒有發明以前,一切書籍全靠手寫傳抄,流傳極為不便;既便是有了印刷術以后,由于歷代的水火兵災戰亂的破壞,加上編次整理不得其法,故書籍不易保存下來。有些學者,為了看到原書的內容和面貌,便把其他書籍引用的該書材料,重新搜輯、整理出來,這項工作,便稱為“輯佚”。
輯佚工作與辨偽工作一樣,起于宋代。宋王應麟就輯有《三家詩考》等書。宋代學者不僅開始了輯佚工作,而且提出了一些搜求書籍的方法。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有一篇“書有名亡實不亡論”,稱“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雖亡,而《周易》具在;漢魏吳晉《鼓吹曲》雖亡,而《樂府》具在;《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十三代史目錄》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凡此之類,名雖亡而實不亡也。”明人祁承業在《澹生堂藏書公約》中說:“書有不亡于漢者,漢人之引經多據之;亡于唐者,唐人之著述尚有之;亡于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從其書各為錄出,不但吉光片羽,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于前者。”此番話雖是針對購書而言,實為承繼鄭樵的思想,把輯佚書的方法更加具體化了。也
明代的輯佚書有馮可賓的《廣百川學海》、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等,多輯自類書,但是真偽參半,考訂未密,漏洞頗多。到了清代,考訂古籍,輯佚辨偽,盛于一時,尤其是《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了很多亡佚的古籍。清代對古書的纂輯鑒別的方法也比較細致。收集輯書最著名的有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搜集已佚的古籍五百八十余種;其次為黃奭的《漢學堂從書》,輯佚約二百五十余種;王謨《漢魏遺書鈔》雖未完成全書,但所列目錄已有四百余種。清代學者有專門從事輯佚古書的工作的,也有為研究某一門學問而致力于某一類專門書籍的輯錄。清人輯錄的專門書籍主要有如下四項:
(一)古代史書:《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中所著錄的“七家后漢書”、“十八家晉史”等,佚失已久,清人姚之骃有《后漢書補遺》,湯球輯有《十六國春秋》,邵晉涵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舊五代史》等。(二)目錄書:目錄書是研究學術源流的主要依據之一,清人章宗源、姚振宗致力于此項工作。姚振宗著有《漢書藝文志條理》和《拾補》,章宗源有《隋書經籍志考證》等,秦嘉謨有宋《崇文總目》輯本。(三)漢魏以來的地理方志:地理方志書籍,可以考見歷代的地方文獻,保存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但零星記載,亡佚尤多。這方面有王謨輯的《漢唐地理書鈔》,張澍《二酉堂叢書》專輯古代西北地理;輯紹興古代地方文獻的有魯迅先生的《會稽郡故書錄》等。(四)六朝以前文集:明張溥所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搜輯既未完備,也有偽誤的地方。清代考據學家嚴可均,盡其平生力量,輯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六朝以前的文章,大體具備。
輯佚工作,雖然主要是針對古代文獻的搜輯,但是近代以來所形成的書籍文獻及檔案文件的亡佚現象也時有發生,如太平天國運動所產生的檔案的大部或為清軍破壞,或在戰火中毀棄;又如省港大罷工的領導機構省港罷工委員會,形成不少檔案文件,但該會在東園的總部發生火災,所存五、六萬份檔案原件,盡成灰燼。等等。類似情況造成的檔案原件的亡佚現象很多。因此,在具體的編研工作中,搜集輯錄已經散佚的檔案文件,也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關于輯佚的方法:第一、要搜輯完備,對一部書或某一專題檔案文件的輯錄,要盡可能多地搜集相關材料中,輯錄力求完整,避免脫漏。第二要考訂準確,輯錄古書或檔案,并不是有文必錄,對輯錄的內容要經過審慎的考證,如以他書所引用的材料作為輯佚的根據,若審核不精,便容易妄加鈔輯,和原書毫不相干,引出的問題,更為嚴重。如劉向所著《別錄》、劉歆《七略》早已亡佚,清人嚴可均的輯本和馬國翰的輯本,據張舜徽先生考證,就發現其中有不少錯誤:“錯誤地把古書上面的文字,看成劉向《別錄》。例如《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云: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治子曰:‘吾嘗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黿也。’這是《晏子春秋》的原文,馬國翰卻誤認為是劉向所作《晏子春秋敘錄》,加以采輯了。”[⑤] 致誤的原因,是輯錄者不解“劉向敘《晏子春秋》”一句中的“敘”字,“敘”在這里作“整理”解,馬國翰把它看作是“敘錄”的敘,因有此誤。這是由于審核不精的結果。第三、根據原書體例,盡量保持原書風貌。在輯佚時,要了解原書體例、學術源流及編排形式,這樣在處理材料時,才能做到心中有數。若將所有材料不加釐別地堆徹在一起,就背離了恢復原書面貌的輯佚目的。所以,輯佚并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近人劉炘曾說過:“輯書,并非易事也。非通校讎、精目錄,則偽舛百出。”他曾指出輯書的四大弊病:第一是漏;第二是濫;第三是誤;第四是陋。在輯書時或有漏落;或望文生義,妄加臆斷;或者引用別人轉引的原文,已非原書的詞句;或者未能辨明著者,未加注明,甚至于張冠李戴,錯誤百出。這都是從事輯佚工作時的大忌。
(莊志齡)
[①] 《讀書脞錄續編》卷一“王制西郊當作四郊”條。
[②]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引劉向《別傳》。
[③] 《魯迅全集》三《馬上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頁。
[④] 羅爾綱:“曾國藩奏報攻陷天京事考謬”,載《太平天國史記載訂謬集》,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
[⑤] 張舜徽《古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