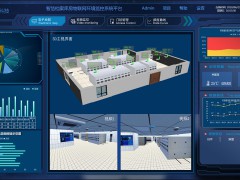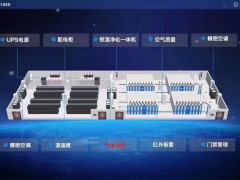五、歷朝起居注與實(shí)錄的編纂
1、起居注的編纂
我國(guó)自古以來(lái)就十分注重對(duì)檔案史料的搜集工作。《禮記·玉藻》稱“天子……玄端而居,動(dòng)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說(shuō):“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當(dāng)然,古代史官的記言記事并不一定有如此嚴(yán)格的分工,但可以肯定的是當(dāng)時(shí)的統(tǒng)治階層已經(jīng)十分重視檔案史料的搜集與儲(chǔ)備工作。到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史官的設(shè)置已十分普遍,甚至卿大夫也置有史官,“趙鞅,晉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guò),操簡(jiǎn)筆于門下。”[i] 齊公子田文,“每坐對(duì)賓客,待史記于屏風(fēng)。”[ii] 古代史官在長(zhǎng)期保管典籍,記錄史事的過(guò)程中,不僅形成了特定的記言、記事的觀點(diǎn)和方法,如董狐、南史氏等甘冒殺頭的危險(xiǎn)“秉筆直書”,忠實(shí)地記載史實(shí),以備后世借鑒。這種記錄文字的日積月累,便成為我們所說(shuō)的檔案史料的主體。同時(shí),進(jìn)入秦漢以后,封建國(guó)家機(jī)構(gòu)日趨完善,史官也逐漸擺脫其他附屬功用,而逐漸成為專門化的職務(wù),這就為起居注一類記載帝王言行的檔案文獻(xiàn)的形成創(chuàng)造了條件。
古代史官有記言記事的分別,秦、漢以后,則合二為一,章學(xué)誠(chéng)所謂“《尚書》入而折為《春秋》”就是這個(gè)意思。據(jù)《漢書·藝文志》載,漢有《著記》一百九十卷,記載了自漢高祖至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共計(jì)十二帝,二百一十一年。其體例即仿《春秋》體例,按年月記錄大事。《后漢書·皇后紀(jì)》引平望侯劉毅的話說(shu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紀(jì)。”又說(shuō)“以太后(和熹鄧皇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紀(jì)”。荀悅《申鑒·時(shí)事篇》說(shuō):“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dòng)靜之節(jié)必書焉。宜復(fù)其式,內(nèi)史掌之,以紀(jì)內(nèi)事。”袁宏《后漢紀(jì)》引靈帝起居注,《隋書·經(jīng)籍志》有獻(xiàn)帝起居注,可知后漢十二帝自光武至獻(xiàn)帝各有起居注。
魏晉時(shí),起居注的修撰工作由著作郎負(fù)責(zé),“著作郎掌起居注,撰錄諸言行勛伐舊載史籍者。”[iii] 北魏時(shí),設(shè)起居令官,“每行幸宴會(huì),則在御左右,記帝王言行及賓客酬對(duì)”。從此,起居注“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起居注類記載,自晉泰始年間到隋開皇之際,共有各代起居注五十部,一千余卷。起居注的記錄為史書的編纂準(zhǔn)備了豐富的史料,梁初吳均撰《齊春秋》時(shí),想借閱齊的起居注,但武帝因其為私家修史,故不許其請(qǐng)。吳均之書,終未能成。可知起居注實(shí)為編撰國(guó)史,尤其是帝王本紀(jì)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資料。
唐代建國(guó),各種制度較之前代更為完善,史官制度也是如此。唐太宗貞觀初年,置起居郎二人,隸門下省,“掌起居注,錄天子言動(dòng)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shí),以時(shí)系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jì)歷數(shù);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guó)史焉。[iv] 高宗顯慶二年,復(fù)置起居舍人二員,隸中書省,“每天子臨軒,侍立于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可見(jiàn),起居注制度在唐代已經(jīng)相當(dāng)完備。
自古以來(lái)“天子不自觀史”是修史制度中的慣例,它可使史官免于外在的干擾,真實(shí)地記錄史事。但是,這一慣例在唐初即遭到了破壞。唐太宗李世民雖然贊賞魏征的直言進(jìn)諫,但對(duì)魏征把有關(guān)君臣爭(zhēng)論之事寫入起居注中的做法卻耿耿于懷。房玄齡修國(guó)史時(shí),唐太宗唯恐于己不利,堅(jiān)持要看起居注,諫議大夫朱子奢稱:“陛下舉事無(wú)過(guò),史官所述,義歸盡善,獨(dú)鑒起居,于事無(wú)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飾非護(hù)短,史官必不免刑株。如此,則莫不希風(fēng)順旨,全身遠(yuǎn)害,悠悠千載,何扎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v] 太宗不聽,逼得房玄齡只有刪改原來(lái)的記載,并對(duì)“宣武門之變”隱約其辭,曲為回護(hù)。由此開了后代君主自觀起居注的惡例。如唐文宗時(shí),鄭朗為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jiàn)朗執(zhí)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zhí)下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hù)失。見(jiàn)之,則史官無(wú)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dòng),非法心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jiàn)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xié)治體,為將來(lái)羞,庶一見(jiàn)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vi] 起居注記載的真實(shí)性遂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壞。
由于起居注只能記朝廷上君臣問(wèn)答之詞,比較機(jī)密的軍國(guó)大事則不可得知,而執(zhí)筆的史官因天子可自觀史而有所忌諱,不敢有聞必錄,而只是采錄敕旨,虛應(yīng)故事,起居注的存史價(jià)值因而大打折扣。武后長(zhǎng)壽年間,宰相姚壽認(rèn)為起居注官不能參聞軍國(guó)大事,“唯得對(duì)仗承旨,仗下后謀議皆不得聞”,而“帝王謨訓(xùn),不可闕于記述,史官疏遠(yuǎn),無(wú)由成書”,建議“請(qǐng)自今而后,所論軍國(guó)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hào)為時(shí)政記。”[vii] 時(shí)政記作為起居注的一種補(bǔ)充形式出現(xiàn)。宰相所撰時(shí)政記每月封送史館,以備修史之用。李吉甫稱時(shí)政記“關(guān)于政化教學(xué),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但時(shí)政記為宰相自撰,難以全為信史。即便如此,時(shí)政記的編撰也是時(shí)行時(shí)綴,“姚壽修于長(zhǎng)壽,及壽罷而事廢;賈耽、齊抗修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以至史官“不復(fù)得聞軍國(guó)大事”,“唯寫誥詞,記除授而已。”[viii] 穆宗長(zhǎng)慶元年,宰相崔植、杜元穎請(qǐng)奏“坐日所有君臣獻(xiàn)替,事關(guān)禮體,便隨日撰錄,號(hào)為圣政記,歲終付史館。” “從之,事亦不行。”[ix] 因此,作為補(bǔ)充起居注記載之不足的時(shí)政記、圣政記基本上未能起到應(yīng)有的作用。
在時(shí)政記、圣政記之外,還有一種“日歷”,即是利用起居注、時(shí)政記等材料整理而成。日歷起于唐憲宗,隸秘書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由此可知,起居注、日歷等均為纂修實(shí)錄、國(guó)史的準(zhǔn)備階段,實(shí)錄、國(guó)史修成以后,其書也就焚毀,故后世皆見(jiàn)不到。唐代從高宗李淵起,歷朝都有起居注的編纂,但現(xiàn)存于世的只有溫大雅編撰的《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三卷。
宋代統(tǒng)治者對(duì)起居注的編撰……
2、實(shí)錄的編纂
實(shí)錄為編年史體之一種,“史官掌修國(guó)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lè)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于起居注,以為實(shí)錄。”[x] 按修史制度,每一帝王死后,史官就根據(jù)起居注或時(shí)政記、日歷等以及官府檔案材料,按年月順序排比編纂大事。實(shí)錄實(shí)際上為一朝檔案史料的匯編,為后世修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基礎(chǔ)。
實(shí)錄最早出現(xiàn)于南朝齊、梁之間,《隋書·經(jīng)籍志》雜史類有周興嗣的《梁皇帝實(shí)錄》三卷,記梁武帝事;謝吳的《梁皇帝實(shí)錄》五卷,記元帝之事,皆為官修。但因早已失傳,故其內(nèi)容體例均已無(wú)從了解。唐初,統(tǒng)治者十分注重修史工作。太宗貞觀三年,“于中書省置秘書內(nèi)省,以修五代史”,并 “別置史館于禁中,專掌國(guó)史,以他官兼領(lǐng),卑品有才,亦以直館,命宰相監(jiān)修,”[xi] 史館的史官在編纂國(guó)史的同時(shí)也參與了實(shí)錄的編纂工作。如吳兢“勵(lì)志強(qiáng)學(xué),博通經(jīng)史。……令直史館,修國(guó)史,累遷右補(bǔ)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shí)錄。”又路隨、韋處厚“嘗在史館,才行可稱,以憲宗實(shí)錄未修,均知論撰,宜兼充史館修撰,仍分日入史館修實(shí)錄。”[xii] 由于統(tǒng)治者對(duì)實(shí)錄編纂工作的重視,因此,自唐代以來(lái),各朝各代都把編纂實(shí)錄視為朝廷大事。每一位皇帝死后,都要根據(jù)當(dāng)朝積累的起居注等檔案史料,以編年體裁編纂一部實(shí)錄。
但是,元代以前的各朝實(shí)錄留傳下來(lái)的極少,除前面提到的唐《順宗實(shí)錄》外,還有北宋錢若水等撰的《宋太宗實(shí)錄》二十卷,但已殘缺不全。主要原因是實(shí)錄卷佚浩繁,僅有鈔本存于禁中,且沒(méi)有皇帝的特許,一般人無(wú)從得見(jiàn)。在朝代更替的戰(zhàn)亂時(shí)代,極易散佚。而且每一新王朝建立,都要編纂前朝史,書成,則實(shí)錄即漸湮沒(méi)。從現(xiàn)存的實(shí)錄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其體例如同編年史的“長(zhǎng)編”,年經(jīng)月緯,將重要事件、制度等分別歸屬,并編入有關(guān)的檔案資料。由于實(shí)錄內(nèi)容十分繁富,凡各種政治設(shè)施、軍事行動(dòng)、經(jīng)濟(jì)措施、自然災(zāi)祥、社會(huì)情況以及帝王婚喪嫁娶、生子命名、祭祀、營(yíng)造等等都有詳細(xì)記錄;至于詔令奏議、百司重要案牘,以及大臣生平事跡,亦均擇要選載。這些材料來(lái)源,既有檔案的依據(jù),又有史館編撰的起居注、時(shí)政記、日歷等作底本,因此事件發(fā)生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一般都記載的比較準(zhǔn)確。盡管其中難免多有曲筆諱飾之處,但史料價(jià)值仍比一般記載為高,為后來(lái)編寫史書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豐富史料。
歷代實(shí)錄比較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只有《明實(shí)錄》和《清實(shí)錄》兩種。
明朝建國(guó),沿襲舊制,置史官掌修國(guó)史。皇帝死后,嗣君即命史官為之修撰實(shí)錄。在二百多年中,共修成了自太祖至熹宗十二朝皇帝實(shí)錄,記載十五帝事跡,共二千九百二十五卷。宗禎實(shí)錄十七卷,為后人補(bǔ)輯而成。《明實(shí)錄》和歷代實(shí)錄一樣,是編年體史料“長(zhǎng)編”,按年、月將事件分別歸屬。在明代各朝的實(shí)錄中,太祖和光宗二朝的實(shí)錄是重修過(guò)的。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曾先后兩次修改《太祖實(shí)錄》,目的在暗示太祖有傳位于他的意圖,甚至否認(rèn)生母為孫妃而說(shuō)為馬后所生。而史官對(duì)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不僅不敢直書,而且多次進(jìn)行篡改,為明成祖非法得位而文飾,以致造成許多疑案,至今不能解決。《光宗實(shí)錄》因閹黨與東林黨的斗爭(zhēng)而被修改,事多失實(shí)。
《明實(shí)錄》撰成后,謄錄正副兩本,正本藏皇史 ,副本藏內(nèi)閣,底稿在太液池邊焚毀,以示禁密。萬(wàn)歷年間因?qū)嶄浘磬^(guò)繁,收藏不易,下令縮小版式,將全部實(shí)錄重抄一遍,一些大臣乘機(jī)私自抄錄,于是流傳于世者漸多。但因輾轉(zhuǎn)傳抄,訛誤脫漏之處頗多。現(xiàn)在流傳者有數(shù)種,唯北京圖書館所藏的為當(dāng)時(shí)的副本,其中缺天啟四年十二卷及七年六月一卷,是為各本中最完善的。
《清實(shí)錄》全稱《大清歷朝實(shí)錄》,從太祖至德宗共十一朝實(shí)錄,加上滿洲實(shí)錄及宣統(tǒng)政紀(jì),共四千四百八十四卷,約三千余萬(wàn)字。清代各朝實(shí)錄原本保存完好,但太祖、太宗與世祖三朝實(shí)錄自修成后,屢經(jīng)修改,愈改愈失其真。在故宮發(fā)現(xiàn)的《太祖皇帝實(shí)錄》和《太祖高皇帝實(shí)錄》以及內(nèi)閣大庫(kù)中發(fā)現(xiàn)的《太祖實(shí)錄》,均為改訂后的廢置本,內(nèi)容與所謂正本的《太祖實(shí)錄》不同。太宗和世祖二朝實(shí)錄舊有鈔本傳世。又有流傳于日本的清三朝實(shí)錄,很多記載與目前通行本不同,據(jù)傳為康熙年間改定本。清統(tǒng)治者反復(fù)修改清初實(shí)錄,意在抹去與明朝的關(guān)系,但明封授女真族的建州三衛(wèi)的史實(shí),在《明實(shí)錄》中都有明確的記載,是無(wú)法完全抹煞的。
因《清實(shí)錄》卷帙浩繁,難于檢閱,乾隆三十年,命蔣良驥從實(shí)錄中摘抄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五帝六朝之事匯為一編,成書三十二卷,因史館地處東華門內(nèi),故稱《東華錄》。蔣良驥所編《東華錄》并不是實(shí)錄的簡(jiǎn)單摘抄本,而補(bǔ)充了許多重要材料,如史可法答攝政王多爾兗書,就為〈實(shí)錄〉所不載;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秀上疏彈劾權(quán)臣明珠,是從郭秀《華野集》中輯錄的。蔣良驥之后,光緒年間,又有王先謙續(xù)纂《東華續(xù)錄》,記乾隆、嘉慶、道光朝事,成書二百三十卷。后又輯有《九朝東華錄》、《十一朝東華錄》的相繼刻印流行。王先謙《東華錄》的資料來(lái)源,據(jù)作者自稱:“凡登載諭旨,恭輯《圣訓(xùn)》、《方略》,編次日月,稽合《本紀(jì)》、《實(shí)錄》;制度沿革纂《會(huì)典》;軍務(wù)折取《方略》。兼載御制詩(shī)文、《大臣列傳》。”增加了不少《實(shí)錄》所無(wú)的材料,如雍正帝辦曾靜一案、咸豐年間鑄大錢事等,王書均較《實(shí)錄》為詳。
宣統(tǒng)元年,朱壽朋撰成《光緒朝東華錄》二百二十卷,起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止于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以邸鈔、京報(bào)和部分中外報(bào)紙記載為主要材料來(lái)源,所載奏章多為全文,為研究中國(guó)近代史的重要資料之一。
[i] 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
[ii] 同上。
[iii] 同上。
[iv] 《舊唐書·職官志》
[v] 《通鑒》卷197《唐紀(jì)》十三
[vi] 《新唐書》卷165《鄭朗傳》
[vii] 《唐會(huì)要·史館》
[viii] 同上。
[ix] 《舊唐書》卷16《穆宗紀(jì)》
[x] 《唐六典》
[xi] 《史通·史官建置》
[xii] 《冊(cè)府元龜·國(guó)史部·選任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