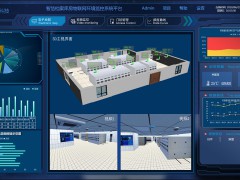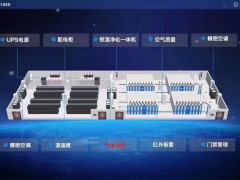三、兩漢時(shí)期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典籍
中國古代發(fā)展到兩漢之際,社會(huì)穩(wěn)定,生產(chǎn)發(fā)展,文化事業(yè)有了長足的進(jìn)步。漢武帝時(shí)曾下書廣求天下藏書,民間獻(xiàn)書活動(dòng)十分踴躍。正如劉歆在《七略》中所稱:“孝武皇帝敕公孫弘廣開獻(xiàn)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i]。根據(jù)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記載,經(jīng)過后來劉氏父子的抉繁剔蕪的整理之后,還有603家,13219卷。 為收藏如此數(shù)量巨大的文獻(xiàn)典籍,不僅皇宮內(nèi)建有“延閣、廣內(nèi)秘室之府”[ii]等藏書庫,一些管理文化教育的部門如“太常、太史、博士”之處也都有秘藏之室。但是,這樣的分散收藏不僅不能使堆積如山的豐富藏書得到很好的開發(fā)利用,反而由于分散保管,使圖書再次散失情況時(shí)時(shí)發(fā)生。這一方面是由于收藏較為分散,皇室、官府各收所藏,互相不通聲氣,另一方面,由于對(duì)書籍從未進(jìn)行過系統(tǒng)的整理,既無具體的量的統(tǒng)計(jì),更無統(tǒng)一的目錄可供查詢,因此,漢室藏書基本上是處在一種混亂的狀態(tài)。這種情況到了漢成帝時(shí),由于有了劉向、劉歆父子的整理,才有所改變。
漢成帝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此時(shí)距漢初開國已有180年的歷史,皇家及官府藏書混亂狀況日趨嚴(yán)重,很多典籍因缺乏有效的管理而散亡。有鑒于此,漢成帝一面下令命謁者陳農(nóng)繼續(xù)“求遺書于天下”,到各地訪求圖書,一面命劉向組織人員從事于典藏文獻(xiàn)的整理。
劉向,字子政,西漢皇室楚元王四世孫,曾任光祿大夫、中壘校尉。他博學(xué)多識(shí),與東漢楊雄齊名,著有《列女傳》,及《新序》、《說苑》等著作。他在接受了整理典籍的任務(wù)后,立即開始了這項(xiàng)繁重的工作。由于搜集上來的典籍從未經(jīng)過整理,凌亂不堪,如何著手開展整理工作,確實(shí)嘎乎其難。劉向根據(jù)自己對(duì)文獻(xiàn)典籍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創(chuàng)立了一套整理文獻(xiàn)典籍的方法。
他首先把所有典籍分六大類(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shù)數(shù)、方技這六類),并根據(jù)參加整理者的專長,按類分派任務(wù)。劉向自己負(fù)責(zé)經(jīng)傳、諸子、詩賦三部分,步兵校尉任宏負(fù)責(zé)整理兵書,太史令尹咸負(fù)責(zé)整理數(shù)術(shù)之書,侍醫(yī)李柱國負(fù)責(zé)方技之書。各部分的工作除有一位主要負(fù)責(zé)人外,還有一些助手參加,如劉歆、杜參、王龔、班斿等人。他們分工合作,進(jìn)行文獻(xiàn)的整理工作。“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iii]。就是說,每一部書校訂完成后,由劉向?qū)懗伞皵洝币黄q如后世的解題、提要、評(píng)述之類。最初每書一篇《敘錄》,寫在本書后面;后來又將群書《敘錄》鈔集在一起,成為一部總的敘錄匯編,以便別行于世,所以又稱為《別錄》。經(jīng)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整個(gè)校書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六大類中所包括的主要圖書都校訂了新本,而每一本也都做了敘錄。劉歆在此基礎(chǔ)上,根據(jù)校訂的圖書和所編寫的敘錄,分門別類,建立了系統(tǒng)的目錄分類,完成了《七略》的撰寫。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七略》被后世史家奉為目錄學(xué)的鼻祖。
劉向、劉歆在總結(jié)利用自孔子以來所創(chuàng)造的文獻(xiàn)編纂整理方法的基礎(chǔ)上,建立了一整套系統(tǒng)的文獻(xiàn)整理和編目方法。其主要程序和方法為:
1、校勘定本 秦以前的文獻(xiàn)典籍,多以單篇形式流傳,不僅極易散失,而且造成了各種不同傳本間的差異。劉向等在整理時(shí),首先把漢秘府兩百年來所積累的藏書,清點(diǎn)一遍,將屬于同一作者或同一部書的各篇集中在一起,如《管子》一書就收集了386種,其中有全本(指篇數(shù)較多)、殘本的單篇。《管子》如此,其他諸子、經(jīng)書也都是如此。誠如劉歆所說:“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iv]。接著,劉向從眾多藏本中選定其中最好的作底本,然后再和其他復(fù)本相校。這是一項(xiàng)極其細(xì)致的工作,劉向稱之為“校讎”,他說:“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duì),故曰讎也。”[v] 校讎時(shí),持底本者把聽到的復(fù)本中的異文脫句記在底本上,使底本的錯(cuò)訛得到初步的澄清。劉向在校訂了底本,編排好篇次之后,就進(jìn)入第二步工作。
2、清繕清本 就是把校訂的底本繕成清本,以便保存和閱讀。劉向在敘錄中經(jīng)常提到“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經(jīng)過研究,人們知道劉向等的底本是在青竹簡上起草的,但“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青竹簡沒有經(jīng)過加工,易折朽或生蠹,無法長久保存,所以必須將青竹簡放在火上烤炙,再用絲繩連編起來。這樣制作的書寫材料保證了文獻(xiàn)典籍的耐久性。
3、編撰敘錄 劉向等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錄就是敘錄,也就是一部書的簡明提要或指南,用以揭示該書的內(nèi)容及相關(guān)信息。劉向等所編撰的敘錄內(nèi)容,有三部分:第一,新定本的篇目;第二,記述校訂過程,包括所依據(jù)的各本的情況如來源、篇數(shù)、文句差謬脫誤情況等;第三,綜述全書大意,包括著者事跡、辨別真?zhèn)我约昂啍兄家獾取_@是敘錄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從現(xiàn)存材料中可以推知,劉向敘錄的每一篇基本如此。
4、分類整理 劉向從一開始校書時(shí)就采取了分類整理典籍的方式。劉向?qū)⑷课墨I(xiàn)分成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shù)數(shù)、方技六大類,經(jīng)過近二十年的努力,六大類的所有圖書文獻(xiàn)都校訂了新本,完成了敘錄的撰寫,每個(gè)大類之下應(yīng)再分多少個(gè)小類,大類和小類所包括的內(nèi)容,大約也有明確的意見和草稿。所以在劉向死后不到兩年,劉歆就完成了《七略》,建成了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目錄。《七略》首篇為《輯略》,是全書的敘錄,說明每個(gè)大類和小類的內(nèi)容和意義。其余“六略”即劉向所分的六大類,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shù)術(shù)略、方技略;“略”下分“種”,計(jì)有38種,630家。這種比較系統(tǒng)、平衡地著錄圖書文獻(xiàn)的方法為后世的文獻(xiàn)整理與編目起到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范文瀾曾評(píng)價(jià)說:“西漢后期,繼司馬遷而起的大博學(xué)家劉向、劉歆父子,做了一個(gè)對(duì)古代文化有巨大貢獻(xiàn)的事業(yè),就是劉向創(chuàng)始劉歆完成的《七略》。”[vi] 劉向、劉歆創(chuàng)立的檔案文獻(xiàn)整理、編目方法對(duì)后世的檔案文獻(xiàn)整理工作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東漢時(shí)明帝任班固為蘭臺(tái)令史,負(fù)責(zé)整理典籍。班固便“依《七略》而為書部”,對(duì)蘭臺(tái)藏書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整理。
[i] 《文選》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劉歆《七略》
[ii] 《太平御覽》卷233引劉歆《七略》。
[iii] 《漢書·藝文志》
[iv] 《漢書》卷36《劉歆本傳》。
[v] 《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太平御覽》卷618引劉向《別錄》。
[vi]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