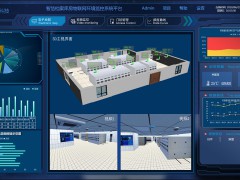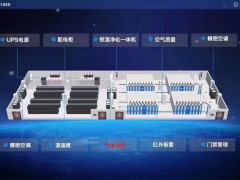海市檔案館石磊
19世紀(jì)前,傳統(tǒng)史學(xué)研究以“今天的歷史即過去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即未來的歷史”作為理論基礎(chǔ)。20世紀(jì)以后,這種具有一定狹隘性的傳統(tǒng)史學(xué)被新史學(xué)所取代。新史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不僅包括上層政治,還包括經(jīng)濟、文化,甚至特定時期內(nèi)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因此,對于新史學(xué)來說,開辟新的史料源變得十分重要。另外,20世紀(jì)特別是20世紀(jì)中期以來,歷史學(xué)與其他學(xué)科交流、融合,充分吸收其他社會科學(xué)或行為科學(xué)理論,使得歷史研究在方法上也發(fā)生了變化。史學(xué)研究出于研究內(nèi)容和研究方法上的需要,開始最大范圍地運用和發(fā)掘檔案史料。當(dāng)代史學(xué)研究新趨勢對檔案利用產(chǎn)生巨大影響,也引發(fā)檔案部門對檔案利用工作新的思考。
一、新史學(xué)流派
(一)法國年鑒學(xué)派
1929年1月中旬,跨學(xué)科的史學(xué)雜志《經(jīng)濟與社會史年鑒》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xué)問世。該雜志由法國歷史學(xué)家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弗爾共同創(chuàng)立,是宣傳他們具有挑戰(zhàn)性的新歷史概念的主要輿論工具,以布洛赫和費弗爾為中心的歷史學(xué)派因此被命名為年鑒學(xué)派。費弗爾堅持認(rèn)為,新歷史學(xué)必須從文字檔案和由文字檔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它必須利用人類的一切創(chuàng)造物如語言、符號、農(nóng)村的證據(jù)、土地制度、項圈、手鐲,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它必須廣泛吸收地理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社會心理學(xué)等其他學(xué)科的發(fā)現(xiàn)和方法。同時它又必須抵制誘惑,防止把自己分割為經(jīng)濟史、思想史這樣各行其是的“專門化”部門。該刊創(chuàng)刊號在《致讀者》中闡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學(xué)科之間的“壁壘”,倡導(dǎo)跨學(xué)科的研究,在繼承傳統(tǒng)和立意創(chuàng)新的基礎(chǔ)上重新認(rèn)識歷史。該學(xué)派明確提出了“問題史學(xué)”的原則,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建立問題、假設(shè)、解釋等程序,從而為引入其他相關(guān)學(xué)科的理論和方法奠定了基礎(chǔ),極大地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lǐng)域。
(二)美國新史學(xué)派
1912年,曾在德國受過嚴(yán)格歷史學(xué)訓(xùn)練的美國歷史學(xué)家魯濱遜首先舉起了“史學(xué)革命”的旗幟,而具體闡釋其“史學(xué)革命”主張的《新史學(xué)》也因此被公認(rèn)為20世紀(jì)世界史學(xué)名著。在這部專著中,他要求沖破以政治史研究為中心的傳統(tǒng),擴大歷史認(rèn)識的視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xí)慣與感情”。他執(zhí)教的哥倫比亞大學(xué)成為美國新史學(xué)的中心,逐漸形成了頗有聲勢的“新史學(xué)派”,一時風(fēng)靡歐美諸國。同一時期,美國歷史學(xué)家通過不斷努力學(xué)習(xí)和創(chuàng)新,也使得他們所取得的成果打上了明顯的美國式烙印。他們首先從歐洲各個學(xué)派那里大量地吸取新思想,尤其是應(yīng)用了馬克斯?韋伯的分析方法和模式。他們采取了社會學(xué)家、政治科學(xué)家、經(jīng)濟學(xué)家的“啟發(fā)式概念”和操作工具。從20世紀(jì)40年代起,他們著手利用社會科學(xué)和行為科學(xué)發(fā)明的度量技術(shù)、方法和成果,并向整個世界證明:數(shù)據(jù)分析、計量技術(shù)、生態(tài)關(guān)聯(lián)、計量經(jīng)濟學(xué)以及其他種種更為成熟的概念工具,在歷史學(xué)家的工作中能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三)英國新社會史學(xué)派
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不僅是科學(xué)共產(chǎn)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20世紀(jì)30年代,即資本主義世界性的經(jīng)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爆發(fā)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影響迅速擴大,正如英國史學(xué)家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樣:到1955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xué)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在歐美各國中,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莫爾頓的《人民的英國史》問世,這是英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得到迅速發(fā)展,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等創(chuàng)立了“新社會史學(xué)派”,強調(diào)研究總體的“社會的歷史”,提出“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等主張,對西方史學(xu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歷史學(xué)新領(lǐng)域和新方法
(一)計量史學(xué)
真正現(xiàn)代意義的計量研究始于二戰(zhàn)以后,它包括三個方面的重要內(nèi)容:一是運用電子計算機,它不僅使得系統(tǒng)收集和利用史料以及進行統(tǒng)計分析成為可能,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處理情報資料和分析多變量信息的能力;二是進行統(tǒng)計分析,這里所說的統(tǒng)計分析不是指以往史學(xué)研究中的描述性統(tǒng)計,而是高級推理統(tǒng)計學(xué)和多變量解析領(lǐng)域的分析;三是制作數(shù)學(xué)模型,借助社會科學(xué)尤其是經(jīng)濟學(xué)中的理論模型,用數(shù)理形式來表現(xiàn)歷史文化現(xiàn)象。計量史學(xué)萌芽于20世紀(jì)30年代的法國,經(jīng)濟學(xué)家西米昂運用計量方法分析貨幣流通的變化,奠定了該學(xué)科的基礎(chǔ)。之后歷史學(xué)家拉布盧斯進一步完善和發(fā)展了西米昂的方法,并把它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去。在美國,20世紀(jì)40年代以后出現(xiàn)了以廣泛采用計量方法和數(shù)學(xué)分析為特征的新史學(xué)。
(二)口述史學(xué)
現(xiàn)代意義的口述史學(xué)發(fā)端于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60年代呈迅猛發(fā)展之勢。作為歷史學(xué)新學(xué)科,口述史學(xué)有其規(guī)范性的操作程序,它通過有計劃的訪談和錄音,對某一個特定的問題獲取第一手口述證據(jù),然后再經(jīng)過篩選和比照,進行歷史研究。口述史學(xué)繁榮的原因,一是由于在“自下而上”歷史觀的指引下,歷史學(xué)家注重關(guān)心普通人的生活;二是由于現(xiàn)代錄音技術(shù)、廉價錄音設(shè)備的普遍推廣。口述史學(xué)的最主要特點在于生動性,其史料來源于普通民眾,展現(xiàn)的是貼近生活的凡人凡事,運用的是雅俗共賞的大眾語言,歷史編撰者和史料提供者共同成為史學(xué)研究過程中的參與者。
(三)影視史學(xué)
影視史學(xué)是當(dāng)代歐美史學(xué)大家族中的一個新生兒。1988年,美國歷史學(xué)家海登?懷特首創(chuàng)了“影視史學(xué)”(Historiophoty)這一新名詞,希望通過視覺影像和相配套的話語傳達歷史以及對歷史的見解。影視史學(xué)不僅僅是電影、電視等新媒體與歷史相交匯的產(chǎn)物,它所指的影像還包括靜態(tài)平面的照片和圖畫,立體造型的雕塑、建筑等。所有傳達視覺影像和聽覺音響的媒體,只要能夠呈現(xiàn)歷史論述,都是影視史學(xué)的研究對象。
三、檔案利用新趨勢及其影響
史學(xué)研究新領(lǐng)域的開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必然會使得可供利用的檔案的范圍也相應(yīng)擴大。這一新趨勢的主要特點表現(xiàn)為:
(一)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內(nèi)容上更趨廣泛
史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拓展使得可供利用的檔案史料范圍從政治、軍事方面向社會、文化甚至人的心理等相關(guān)內(nèi)容拓展。以1975年在法國出版的一部典型心態(tài)史研究論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為例。①這部論著的作者是曾任法國國立圖書館館長達6年之久的勒華拉杜里。勒華拉杜里因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梵蒂岡圖書館內(nèi)發(fā)現(xiàn)了一批13世紀(jì)地方宗教裁判所的檔案。1320年,當(dāng)時任帕米埃主教的雅克?富尼埃作為宗教裁判所法官在蒙塔尤調(diào)查、審理各種案件,并留下了578件詳細記錄。由于在審判過程中對這些“罪犯”反復(fù)盤問,特別是對他們的信仰、道德行為、社會聯(lián)系等細節(jié)都不輕易放過,勒華拉杜里敏感地意識到這批檔案“為研究農(nóng)村普通人民的精神觀念提供了機會”。他援引這批檔案試圖還原的并不是有關(guān)某個異端宗派的宗教史,而是使用“農(nóng)民自已提供的證詞”再現(xiàn)蒙塔尤的農(nóng)民的日常生活、社會關(guān)系、宗教信仰、習(xí)俗禮儀、個人隱私等社區(qū)生活,來重現(xiàn)普通農(nóng)民的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世界。
這種趨勢在當(dāng)前中國檔案館的學(xué)術(shù)研究利用者身上有明顯體現(xiàn)。以上海市檔案館1993年至2000年所接待的474批境外利用者為分析對象,其中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的有432批,約占91.1%;新聞媒體有14批,約占3%;其他利用者27批,約占5.7%。432批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的境外利用者主要研究政治史、經(jīng)濟史(含工商企業(yè)、金融、貿(mào)易)、文化史(含教育、衛(wèi)生、體育)、社會史、宗教史和租界史。其中研究政治史的學(xué)者93批,約占21.5%;研究經(jīng)濟史的學(xué)者120批,約占27.8%;研究文化教育史的學(xué)者101批,約占23.4%;從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學(xué)者有118批,約占27.3%,而在這118批學(xué)者中,有的研究人物,有的研究外僑團體,有的研究社會福利、慈善機構(gòu),有的研究民俗、婚姻。所利用檔案在內(nèi)容上有明顯的廣泛性。
(二)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性質(zhì)上更趨多樣
歷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往往同材料與方法的運用密切相關(guān):新材料能激發(fā)新方法的援用,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當(dāng)然也包括舊材料)得到更高層次上的解釋。史學(xué)研究新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技術(shù)設(shè)備的運用,它使得各種性質(zhì)的檔案都可以被納入史料范圍。以往的歷史研究可能偏重于從行政檔案、企業(yè)檔案中的文書材料中挖掘史料;而在當(dāng)代,檔案史料的選材范圍可以擴大到各種訴訟檔案、會計檔案、商標(biāo)檔案、地名檔案、人口普查檔案等等。正如在2003年召開的第35屆國際檔案圓桌會議第4次會議上,一位名為A?C?得布朗的檔案工作者在他提交的報告《匈牙利和阿根廷的新歷史和私人檔案》中總結(jié)指出的那樣:“研究者對檔案資料的全面性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們應(yīng)從現(xiàn)在起對這一問題加以重視。現(xiàn)在似乎任何一件檔案都可能成為有趣的焦點,幫助學(xué)者從新的角度研究歷史。僅僅是公眾人物的檔案是不夠的,那些‘街上的百姓’也很有趣。”②
這一點在計量史學(xué)研究方面最為突出。計量史學(xué)家在電腦的幫助下,“可以最大限度地運用與發(fā)掘史料,這是傳統(tǒng)的以定性分析的描述方法所無法解決的,”“新的史料被源源不斷地發(fā)掘出來,諸如選民登記、教區(qū)檔案、法庭記錄、公私帳簿、公私藏書目錄、病史記錄、結(jié)婚登記、死者遺囑、家譜、稅單等等,都可以視為‘史料’。”③
(三)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載體和記錄形式上發(fā)生變化
口述史學(xué)和影視史學(xué)的出現(xiàn),使得紙質(zhì)載體的文獻檔案之外的其他載體檔案和其他記錄形式檔案也將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到史學(xué)研究中去。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刊《逗號》新近出版的有關(guān)土著民族的專刊中刊登了10篇文章,其中4篇涉及到以口述檔案記錄土著民族歷史,1篇涉及到以音像檔案記錄土著民族的歷史,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地區(qū)當(dāng)?shù)氐囊晃粰n案工作人員所說:“數(shù)字?jǐn)z像的形式使我們能夠?qū)n案與健在的老人的聲音結(jié)合起來,再現(xiàn)Dane-zaa講故事的劇場效果。”④
口述史學(xué)雖然在史學(xué)界尚未成為主流,但是它并不是新生事物。在《檔案開發(fā)與利用教程》中,作者就將“檔案史料”劃分為“口碑檔案”、“文物檔案”、“文獻檔案”,并且指出:“口碑檔案雖然史實與神話共雜,但它畢竟有其歷史的內(nèi)核和要素,因此可資后人分析利用。”⑤故老相傳的口碑檔案與現(xiàn)代人的口述材料在可信度上雖然不同,但是都可以作為檔案史料來加以利用卻是它們的共同點。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xué)珍本和手稿圖書館內(nèi)就收藏有大量中國口述歷史資料。它的入選人員的范圍包括:政府高級官員、軍事領(lǐng)導(dǎo)者、反對黨領(lǐng)導(dǎo)人、社會有影響的人士等。根據(jù)這?原則,哥大東亞研究所對17個民國時期的重要人物進行采訪,整理了近3萬頁口述材料;另外,臺灣近代史研究所也大力從事口述歷史的記錄和整理,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期間完成的41人口述資料已經(jīng)作為禮物被贈送哥大。⑥
如果說反映歷史題材的紀(jì)錄片能夠納入影視史學(xué)的范疇,那么影視史學(xué)在當(dāng)代中國進一步發(fā)展,并且與檔案史料有效結(jié)合的典型例子也有不少。根據(jù)中央檔案館珍藏檔案制作而成的電視片《紅旗飄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今天》是中國共產(chǎn)黨80年歷史的全面生動的展現(xiàn)。該劇分為365集,以一年的時間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80多家電視臺播出,觀眾達到1.7億人。2000年下半年,中央電視臺制作的又一部大型文獻紀(jì)錄片《百年中國》在中央一套播出,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3年,由上海市檔案局主持拍攝,反映上海獨特城市發(fā)展風(fēng)貌的百集紀(jì)實專題片《追憶--檔案里的故事》第一期30集在上視紀(jì)實頻道以一天一集的形式播出。該片一經(jīng)推出就創(chuàng)下了上海地區(qū)專題片收視率新高。據(jù)央視索福瑞數(shù)據(jù)調(diào)查顯示,該片播出30天中有21天排名在上視紀(jì)實頻道當(dāng)天收視率前10名以內(nèi),其中有2天排名第一。專家學(xué)者們普遍肯定該片“史料翔實、語言平穩(wěn)、脈絡(luò)清晰,精美完整地再現(xiàn)了近代上海的城市與生活,是了解上海歷史發(fā)展的不可多得的生動教材。”⑦
口述史學(xué)和影視史學(xué)的發(fā)展對檔案編研工作也產(chǎn)生一定影響。20世紀(jì)以來,大眾傳媒的發(fā)展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在沒有廣播、影視、互聯(lián)網(wǎng)的時代,人們主要通過書籍和報刊雜志獲取信息,因此檔案編研產(chǎn)品也主要是以書刊的形式出現(xiàn);廣播、影視、互聯(lián)網(wǎng)不僅具有和書刊一樣的信息傳播功能,而且它們具有超越書籍的傳播優(yōu)勢。因此,有學(xué)者指出:“檔案文獻編纂公布活動應(yīng)當(dāng)保持與大眾傳媒的‘共進’,根據(jù)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人民活動方式的轉(zhuǎn)變,在繼承以往編纂經(jīng)驗和形式的基礎(chǔ)上,積極從編纂形式、傳播途徑、用戶心理等方面探尋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發(fā)展方向和規(guī)律,對檔案信息進行全新的思想整合”。⑧
注釋:
①參見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前言,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版。
②國家檔案局外事辦編印:《外國檔案工作動態(tài)》,2003年4月第2期。
③張廣智:《西方史學(xué)史》,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頁。
④參見《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刊<逗號>檔案與土著民族專刊文章摘要》,國家檔案局外事辦編印《外國檔案工作動態(tài)》,2003年8月第6期。
⑤劉耿生:《檔案開發(fā)與利用教程》,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頁。
⑥參見楊天石:《美國訪史雜記》,《檔案與史學(xué)》1994年第1期。
⑦樊琳:《搶眼的上海歷史印痕?<追憶?檔案里的故事>拍攝隨想》,《檔案與史學(xué)》2003年第3期。
⑧丁華東:《文獻紀(jì)錄片的繁榮帶給我們的理性思考》,《上海檔案》2002年第1期。
19世紀(jì)前,傳統(tǒng)史學(xué)研究以“今天的歷史即過去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即未來的歷史”作為理論基礎(chǔ)。20世紀(jì)以后,這種具有一定狹隘性的傳統(tǒng)史學(xué)被新史學(xué)所取代。新史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不僅包括上層政治,還包括經(jīng)濟、文化,甚至特定時期內(nèi)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因此,對于新史學(xué)來說,開辟新的史料源變得十分重要。另外,20世紀(jì)特別是20世紀(jì)中期以來,歷史學(xué)與其他學(xué)科交流、融合,充分吸收其他社會科學(xué)或行為科學(xué)理論,使得歷史研究在方法上也發(fā)生了變化。史學(xué)研究出于研究內(nèi)容和研究方法上的需要,開始最大范圍地運用和發(fā)掘檔案史料。當(dāng)代史學(xué)研究新趨勢對檔案利用產(chǎn)生巨大影響,也引發(fā)檔案部門對檔案利用工作新的思考。
一、新史學(xué)流派
(一)法國年鑒學(xué)派
1929年1月中旬,跨學(xué)科的史學(xué)雜志《經(jīng)濟與社會史年鑒》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xué)問世。該雜志由法國歷史學(xué)家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弗爾共同創(chuàng)立,是宣傳他們具有挑戰(zhàn)性的新歷史概念的主要輿論工具,以布洛赫和費弗爾為中心的歷史學(xué)派因此被命名為年鑒學(xué)派。費弗爾堅持認(rèn)為,新歷史學(xué)必須從文字檔案和由文字檔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它必須利用人類的一切創(chuàng)造物如語言、符號、農(nóng)村的證據(jù)、土地制度、項圈、手鐲,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它必須廣泛吸收地理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社會心理學(xué)等其他學(xué)科的發(fā)現(xiàn)和方法。同時它又必須抵制誘惑,防止把自己分割為經(jīng)濟史、思想史這樣各行其是的“專門化”部門。該刊創(chuàng)刊號在《致讀者》中闡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學(xué)科之間的“壁壘”,倡導(dǎo)跨學(xué)科的研究,在繼承傳統(tǒng)和立意創(chuàng)新的基礎(chǔ)上重新認(rèn)識歷史。該學(xué)派明確提出了“問題史學(xué)”的原則,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建立問題、假設(shè)、解釋等程序,從而為引入其他相關(guān)學(xué)科的理論和方法奠定了基礎(chǔ),極大地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lǐng)域。
(二)美國新史學(xué)派
1912年,曾在德國受過嚴(yán)格歷史學(xué)訓(xùn)練的美國歷史學(xué)家魯濱遜首先舉起了“史學(xué)革命”的旗幟,而具體闡釋其“史學(xué)革命”主張的《新史學(xué)》也因此被公認(rèn)為20世紀(jì)世界史學(xué)名著。在這部專著中,他要求沖破以政治史研究為中心的傳統(tǒng),擴大歷史認(rèn)識的視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xí)慣與感情”。他執(zhí)教的哥倫比亞大學(xué)成為美國新史學(xué)的中心,逐漸形成了頗有聲勢的“新史學(xué)派”,一時風(fēng)靡歐美諸國。同一時期,美國歷史學(xué)家通過不斷努力學(xué)習(xí)和創(chuàng)新,也使得他們所取得的成果打上了明顯的美國式烙印。他們首先從歐洲各個學(xué)派那里大量地吸取新思想,尤其是應(yīng)用了馬克斯?韋伯的分析方法和模式。他們采取了社會學(xué)家、政治科學(xué)家、經(jīng)濟學(xué)家的“啟發(fā)式概念”和操作工具。從20世紀(jì)40年代起,他們著手利用社會科學(xué)和行為科學(xué)發(fā)明的度量技術(shù)、方法和成果,并向整個世界證明:數(shù)據(jù)分析、計量技術(shù)、生態(tài)關(guān)聯(lián)、計量經(jīng)濟學(xué)以及其他種種更為成熟的概念工具,在歷史學(xué)家的工作中能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三)英國新社會史學(xué)派
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不僅是科學(xué)共產(chǎn)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20世紀(jì)30年代,即資本主義世界性的經(jīng)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爆發(fā)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影響迅速擴大,正如英國史學(xué)家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樣:到1955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xué)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在歐美各國中,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莫爾頓的《人民的英國史》問世,這是英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得到迅速發(fā)展,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等創(chuàng)立了“新社會史學(xué)派”,強調(diào)研究總體的“社會的歷史”,提出“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等主張,對西方史學(xu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歷史學(xué)新領(lǐng)域和新方法
(一)計量史學(xué)
真正現(xiàn)代意義的計量研究始于二戰(zhàn)以后,它包括三個方面的重要內(nèi)容:一是運用電子計算機,它不僅使得系統(tǒng)收集和利用史料以及進行統(tǒng)計分析成為可能,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處理情報資料和分析多變量信息的能力;二是進行統(tǒng)計分析,這里所說的統(tǒng)計分析不是指以往史學(xué)研究中的描述性統(tǒng)計,而是高級推理統(tǒng)計學(xué)和多變量解析領(lǐng)域的分析;三是制作數(shù)學(xué)模型,借助社會科學(xué)尤其是經(jīng)濟學(xué)中的理論模型,用數(shù)理形式來表現(xiàn)歷史文化現(xiàn)象。計量史學(xué)萌芽于20世紀(jì)30年代的法國,經(jīng)濟學(xué)家西米昂運用計量方法分析貨幣流通的變化,奠定了該學(xué)科的基礎(chǔ)。之后歷史學(xué)家拉布盧斯進一步完善和發(fā)展了西米昂的方法,并把它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去。在美國,20世紀(jì)40年代以后出現(xiàn)了以廣泛采用計量方法和數(shù)學(xué)分析為特征的新史學(xué)。
(二)口述史學(xué)
現(xiàn)代意義的口述史學(xué)發(fā)端于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60年代呈迅猛發(fā)展之勢。作為歷史學(xué)新學(xué)科,口述史學(xué)有其規(guī)范性的操作程序,它通過有計劃的訪談和錄音,對某一個特定的問題獲取第一手口述證據(jù),然后再經(jīng)過篩選和比照,進行歷史研究。口述史學(xué)繁榮的原因,一是由于在“自下而上”歷史觀的指引下,歷史學(xué)家注重關(guān)心普通人的生活;二是由于現(xiàn)代錄音技術(shù)、廉價錄音設(shè)備的普遍推廣。口述史學(xué)的最主要特點在于生動性,其史料來源于普通民眾,展現(xiàn)的是貼近生活的凡人凡事,運用的是雅俗共賞的大眾語言,歷史編撰者和史料提供者共同成為史學(xué)研究過程中的參與者。
(三)影視史學(xué)
影視史學(xué)是當(dāng)代歐美史學(xué)大家族中的一個新生兒。1988年,美國歷史學(xué)家海登?懷特首創(chuàng)了“影視史學(xué)”(Historiophoty)這一新名詞,希望通過視覺影像和相配套的話語傳達歷史以及對歷史的見解。影視史學(xué)不僅僅是電影、電視等新媒體與歷史相交匯的產(chǎn)物,它所指的影像還包括靜態(tài)平面的照片和圖畫,立體造型的雕塑、建筑等。所有傳達視覺影像和聽覺音響的媒體,只要能夠呈現(xiàn)歷史論述,都是影視史學(xué)的研究對象。
三、檔案利用新趨勢及其影響
史學(xué)研究新領(lǐng)域的開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必然會使得可供利用的檔案的范圍也相應(yīng)擴大。這一新趨勢的主要特點表現(xiàn)為:
(一)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內(nèi)容上更趨廣泛
史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拓展使得可供利用的檔案史料范圍從政治、軍事方面向社會、文化甚至人的心理等相關(guān)內(nèi)容拓展。以1975年在法國出版的一部典型心態(tài)史研究論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為例。①這部論著的作者是曾任法國國立圖書館館長達6年之久的勒華拉杜里。勒華拉杜里因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梵蒂岡圖書館內(nèi)發(fā)現(xiàn)了一批13世紀(jì)地方宗教裁判所的檔案。1320年,當(dāng)時任帕米埃主教的雅克?富尼埃作為宗教裁判所法官在蒙塔尤調(diào)查、審理各種案件,并留下了578件詳細記錄。由于在審判過程中對這些“罪犯”反復(fù)盤問,特別是對他們的信仰、道德行為、社會聯(lián)系等細節(jié)都不輕易放過,勒華拉杜里敏感地意識到這批檔案“為研究農(nóng)村普通人民的精神觀念提供了機會”。他援引這批檔案試圖還原的并不是有關(guān)某個異端宗派的宗教史,而是使用“農(nóng)民自已提供的證詞”再現(xiàn)蒙塔尤的農(nóng)民的日常生活、社會關(guān)系、宗教信仰、習(xí)俗禮儀、個人隱私等社區(qū)生活,來重現(xiàn)普通農(nóng)民的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世界。
這種趨勢在當(dāng)前中國檔案館的學(xué)術(shù)研究利用者身上有明顯體現(xiàn)。以上海市檔案館1993年至2000年所接待的474批境外利用者為分析對象,其中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的有432批,約占91.1%;新聞媒體有14批,約占3%;其他利用者27批,約占5.7%。432批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的境外利用者主要研究政治史、經(jīng)濟史(含工商企業(yè)、金融、貿(mào)易)、文化史(含教育、衛(wèi)生、體育)、社會史、宗教史和租界史。其中研究政治史的學(xué)者93批,約占21.5%;研究經(jīng)濟史的學(xué)者120批,約占27.8%;研究文化教育史的學(xué)者101批,約占23.4%;從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學(xué)者有118批,約占27.3%,而在這118批學(xué)者中,有的研究人物,有的研究外僑團體,有的研究社會福利、慈善機構(gòu),有的研究民俗、婚姻。所利用檔案在內(nèi)容上有明顯的廣泛性。
(二)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性質(zhì)上更趨多樣
歷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往往同材料與方法的運用密切相關(guān):新材料能激發(fā)新方法的援用,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當(dāng)然也包括舊材料)得到更高層次上的解釋。史學(xué)研究新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技術(shù)設(shè)備的運用,它使得各種性質(zhì)的檔案都可以被納入史料范圍。以往的歷史研究可能偏重于從行政檔案、企業(yè)檔案中的文書材料中挖掘史料;而在當(dāng)代,檔案史料的選材范圍可以擴大到各種訴訟檔案、會計檔案、商標(biāo)檔案、地名檔案、人口普查檔案等等。正如在2003年召開的第35屆國際檔案圓桌會議第4次會議上,一位名為A?C?得布朗的檔案工作者在他提交的報告《匈牙利和阿根廷的新歷史和私人檔案》中總結(jié)指出的那樣:“研究者對檔案資料的全面性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們應(yīng)從現(xiàn)在起對這一問題加以重視。現(xiàn)在似乎任何一件檔案都可能成為有趣的焦點,幫助學(xué)者從新的角度研究歷史。僅僅是公眾人物的檔案是不夠的,那些‘街上的百姓’也很有趣。”②
這一點在計量史學(xué)研究方面最為突出。計量史學(xué)家在電腦的幫助下,“可以最大限度地運用與發(fā)掘史料,這是傳統(tǒng)的以定性分析的描述方法所無法解決的,”“新的史料被源源不斷地發(fā)掘出來,諸如選民登記、教區(qū)檔案、法庭記錄、公私帳簿、公私藏書目錄、病史記錄、結(jié)婚登記、死者遺囑、家譜、稅單等等,都可以視為‘史料’。”③
(三)可作為史料的檔案在載體和記錄形式上發(fā)生變化
口述史學(xué)和影視史學(xué)的出現(xiàn),使得紙質(zhì)載體的文獻檔案之外的其他載體檔案和其他記錄形式檔案也將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到史學(xué)研究中去。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刊《逗號》新近出版的有關(guān)土著民族的專刊中刊登了10篇文章,其中4篇涉及到以口述檔案記錄土著民族歷史,1篇涉及到以音像檔案記錄土著民族的歷史,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地區(qū)當(dāng)?shù)氐囊晃粰n案工作人員所說:“數(shù)字?jǐn)z像的形式使我們能夠?qū)n案與健在的老人的聲音結(jié)合起來,再現(xiàn)Dane-zaa講故事的劇場效果。”④
口述史學(xué)雖然在史學(xué)界尚未成為主流,但是它并不是新生事物。在《檔案開發(fā)與利用教程》中,作者就將“檔案史料”劃分為“口碑檔案”、“文物檔案”、“文獻檔案”,并且指出:“口碑檔案雖然史實與神話共雜,但它畢竟有其歷史的內(nèi)核和要素,因此可資后人分析利用。”⑤故老相傳的口碑檔案與現(xiàn)代人的口述材料在可信度上雖然不同,但是都可以作為檔案史料來加以利用卻是它們的共同點。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xué)珍本和手稿圖書館內(nèi)就收藏有大量中國口述歷史資料。它的入選人員的范圍包括:政府高級官員、軍事領(lǐng)導(dǎo)者、反對黨領(lǐng)導(dǎo)人、社會有影響的人士等。根據(jù)這?原則,哥大東亞研究所對17個民國時期的重要人物進行采訪,整理了近3萬頁口述材料;另外,臺灣近代史研究所也大力從事口述歷史的記錄和整理,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期間完成的41人口述資料已經(jīng)作為禮物被贈送哥大。⑥
如果說反映歷史題材的紀(jì)錄片能夠納入影視史學(xué)的范疇,那么影視史學(xué)在當(dāng)代中國進一步發(fā)展,并且與檔案史料有效結(jié)合的典型例子也有不少。根據(jù)中央檔案館珍藏檔案制作而成的電視片《紅旗飄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今天》是中國共產(chǎn)黨80年歷史的全面生動的展現(xiàn)。該劇分為365集,以一年的時間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80多家電視臺播出,觀眾達到1.7億人。2000年下半年,中央電視臺制作的又一部大型文獻紀(jì)錄片《百年中國》在中央一套播出,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3年,由上海市檔案局主持拍攝,反映上海獨特城市發(fā)展風(fēng)貌的百集紀(jì)實專題片《追憶--檔案里的故事》第一期30集在上視紀(jì)實頻道以一天一集的形式播出。該片一經(jīng)推出就創(chuàng)下了上海地區(qū)專題片收視率新高。據(jù)央視索福瑞數(shù)據(jù)調(diào)查顯示,該片播出30天中有21天排名在上視紀(jì)實頻道當(dāng)天收視率前10名以內(nèi),其中有2天排名第一。專家學(xué)者們普遍肯定該片“史料翔實、語言平穩(wěn)、脈絡(luò)清晰,精美完整地再現(xiàn)了近代上海的城市與生活,是了解上海歷史發(fā)展的不可多得的生動教材。”⑦
口述史學(xué)和影視史學(xué)的發(fā)展對檔案編研工作也產(chǎn)生一定影響。20世紀(jì)以來,大眾傳媒的發(fā)展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在沒有廣播、影視、互聯(lián)網(wǎng)的時代,人們主要通過書籍和報刊雜志獲取信息,因此檔案編研產(chǎn)品也主要是以書刊的形式出現(xiàn);廣播、影視、互聯(lián)網(wǎng)不僅具有和書刊一樣的信息傳播功能,而且它們具有超越書籍的傳播優(yōu)勢。因此,有學(xué)者指出:“檔案文獻編纂公布活動應(yīng)當(dāng)保持與大眾傳媒的‘共進’,根據(jù)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人民活動方式的轉(zhuǎn)變,在繼承以往編纂經(jīng)驗和形式的基礎(chǔ)上,積極從編纂形式、傳播途徑、用戶心理等方面探尋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發(fā)展方向和規(guī)律,對檔案信息進行全新的思想整合”。⑧
注釋:
①參見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前言,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版。
②國家檔案局外事辦編印:《外國檔案工作動態(tài)》,2003年4月第2期。
③張廣智:《西方史學(xué)史》,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頁。
④參見《國際檔案理事會會刊<逗號>檔案與土著民族專刊文章摘要》,國家檔案局外事辦編印《外國檔案工作動態(tài)》,2003年8月第6期。
⑤劉耿生:《檔案開發(fā)與利用教程》,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頁。
⑥參見楊天石:《美國訪史雜記》,《檔案與史學(xué)》1994年第1期。
⑦樊琳:《搶眼的上海歷史印痕?<追憶?檔案里的故事>拍攝隨想》,《檔案與史學(xué)》2003年第3期。
⑧丁華東:《文獻紀(jì)錄片的繁榮帶給我們的理性思考》,《上海檔案》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