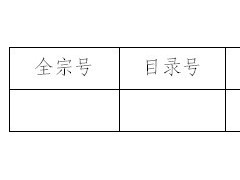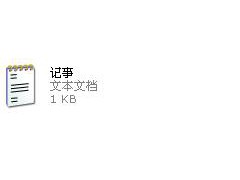檔案的產(chǎn)生是以處理復(fù)雜事務(wù)為目的、以一定的物質(zhì)基礎(chǔ)為載體條件的。在遠(yuǎn)古蠻荒的文明之初,是茹毛飲血的舊石器時(shí)代,投擲、尖劈、杠桿等知識(shí)幫助人們度過(guò)了漫長(zhǎng)的原始社會(huì)。由于生產(chǎn)力極其低下,社會(huì)關(guān)系簡(jiǎn)單,原始社會(huì)早期人們的交往、社會(huì)活動(dòng)僅靠口口相傳就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我國(guó)的遠(yuǎn)古傳說(shuō)十分豐富,如有巢氏架木為巢,燧人氏鉆木取火,伏羲氏結(jié)網(wǎng)捕魚,神農(nóng)氏種植五谷百草等。這些傳說(shuō)使我國(guó)遠(yuǎn)古燦爛的歷史得以流傳。但有了傳說(shuō)并不等于有了檔案。
當(dāng)社會(huì)從低級(jí)原始階段向前發(fā)展時(shí),為適應(yīng)日益復(fù)雜的社會(huì)生產(chǎn)和生活要求,人們開始以實(shí)物幫助記憶,即在物件上做出一些標(biāo)記或符號(hào)表達(dá)思想或記事。我國(guó)歷史上主要有結(jié)繩和刻契等原始記事方法。《易·系辭》載:“上古結(jié)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載:“結(jié)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zhí)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可見(jiàn),結(jié)繩是我國(guó)最早的記事方法。
刻契記事比結(jié)繩記事更進(jìn)一步。所謂刻契,即在木片、骨片或玉片上刻上符號(hào)以記事。這種記事方法在我國(guó)古籍也有記載,如西漢學(xué)者孔安國(guó)《尚書·序》載:“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jié)繩之政。”
刻契記事在我國(guó)一些少數(shù)民族中也能得到印證。如《隋書·突厥傳》載:“無(wú)文字,刻木為‘契’”,說(shuō)明一些少數(shù)民族在文字產(chǎn)生前已有“契”了。到上世紀(jì)50年代,我國(guó)一些少數(shù)民族仍以刻契記事。
原始人還善于用圖畫來(lái)記事,比刻契記事又進(jìn)了一步。傳說(shuō)中,遠(yuǎn)古時(shí)期人們用花、蟲、鳥、獸等各種符號(hào)記錄種種事物。近年我國(guó)出土的原始社會(huì)晚期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彩陶上的刻劃符號(hào),學(xué)者認(rèn)為就是簡(jiǎn)化了的圖畫。
遠(yuǎn)古時(shí)期,人們由于受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和語(yǔ)言文字的限制,盡管借助于各種標(biāo)記、符號(hào),用結(jié)繩、刻契、圖畫等記事方法,能保存、傳遞相關(guān)記錄信息,但由于原始記事方法的局限性,留存的記憶往往是不確切、不完整的,不能成為普遍的社會(huì)交往工具。歷史、語(yǔ)言學(xué)家把這一時(shí)代稱為“助記憶時(shí)代”。然而,原始記事在一定范圍內(nèi)有歷史記錄、契約、憑證、備忘等作用,因此,可以看作是檔案的萌芽,即檔案起源的初始形態(tài)。